台灣人到底怎麼想UBI的
無條件基本收入在台灣遭遇了怎樣的觀念挑戰?
魏嘉佑/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生
想像一個這樣的社會,你無需付出任何的勞動,政府就會每個月發派一筆錢給你,足以支應你的基本生活──這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後文簡稱為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概念,UBI倡議者所認為的理想世界,人們終能享受到真正的「好生活」,過得更加幸福(見圖一、二、三)。但是我身在台灣無條件收入協會(後文簡稱為UBI Taiwan)推廣、研究這項方案,將精力奉獻於我所深信能夠為大部分人帶來「好生活」之國家財富重分配模式的過程中,卻也從和他人的辯談之中發現台灣社會內部對於好生活想像的分歧。

圖一:UBI Taiwan成員們進行街頭宣傳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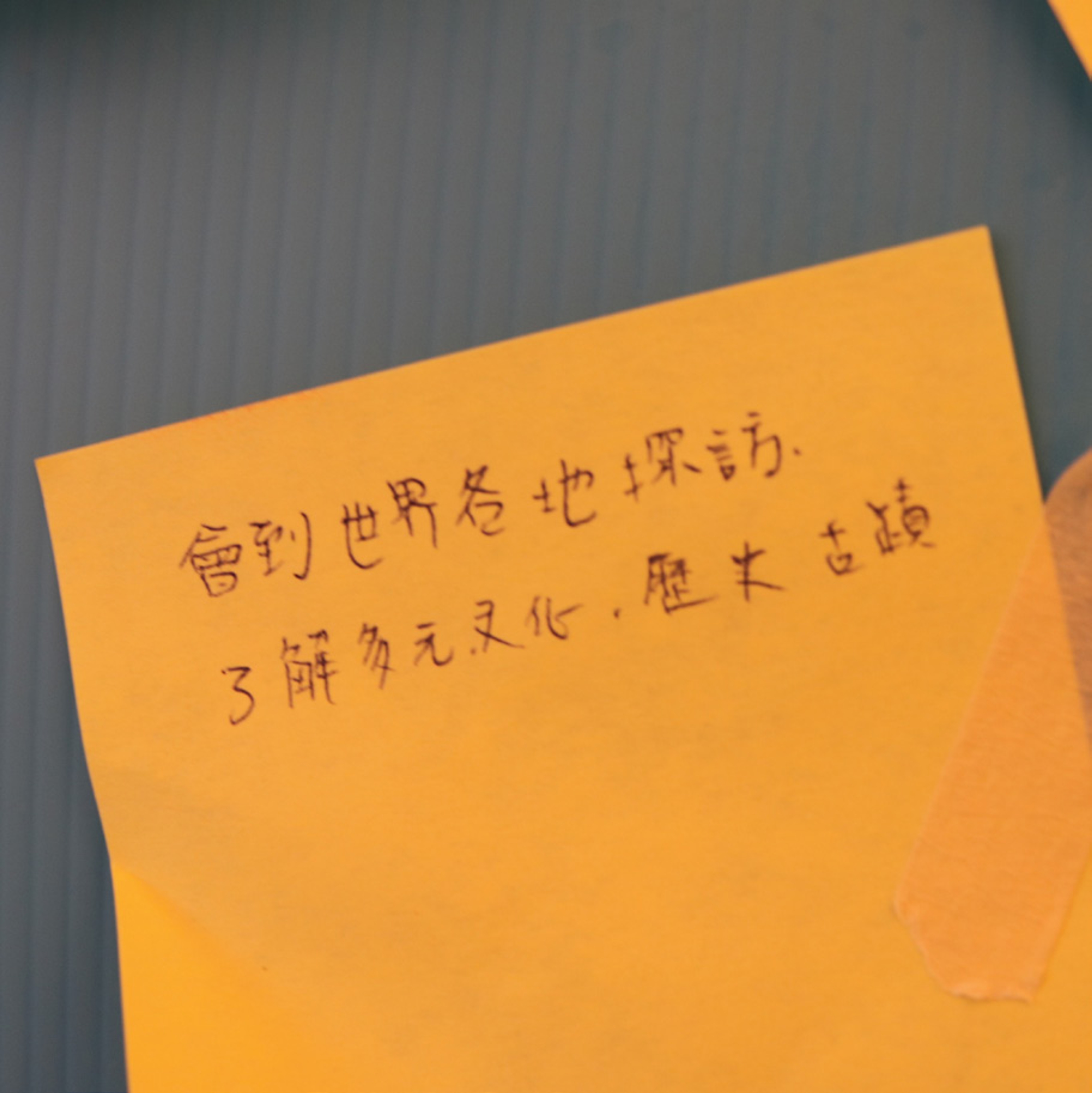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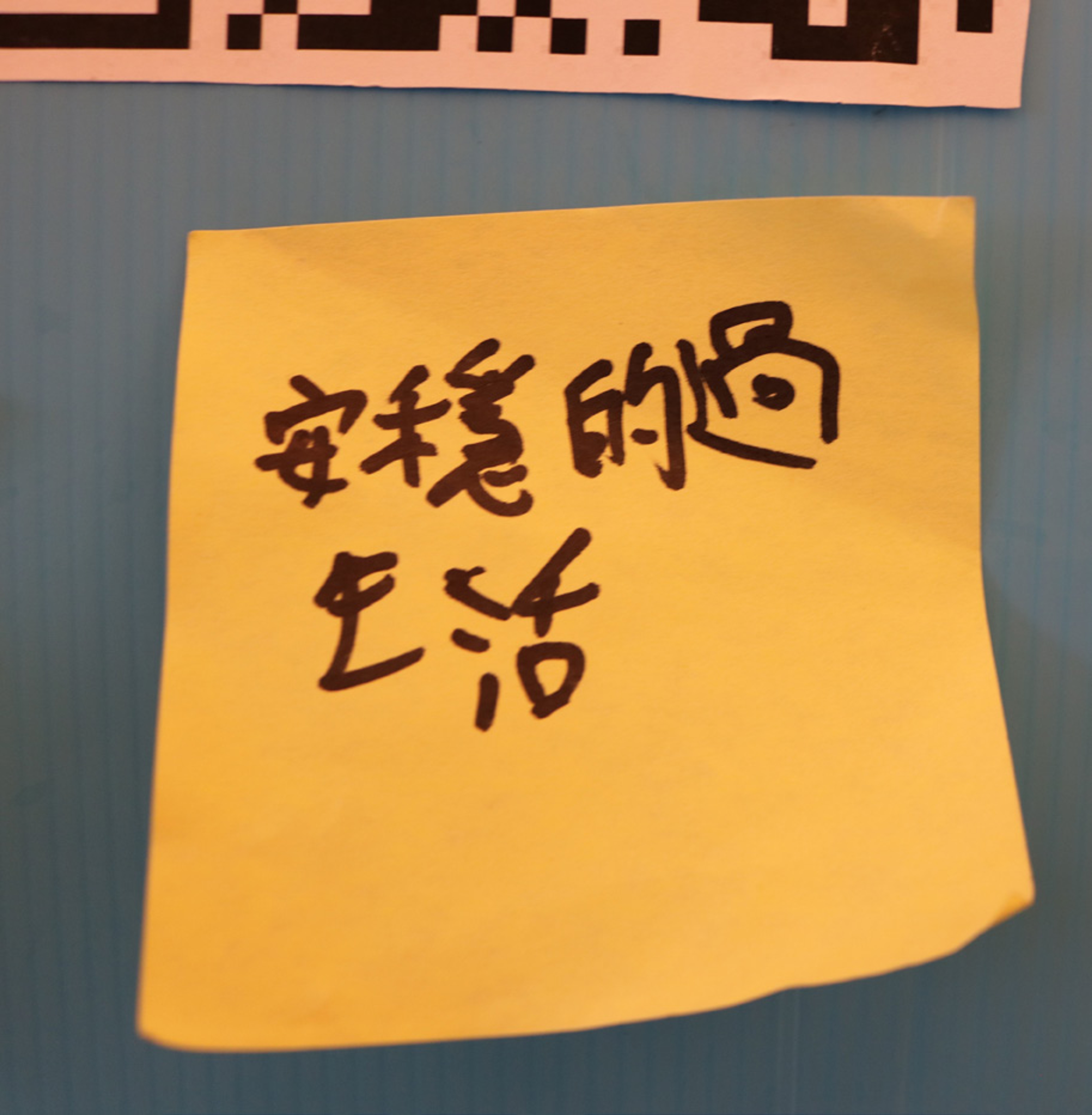
圖二、三:民眾所分享擁有UBI之後的未來「好生活」。
這因此成為我撰寫本文的源由,讓我決定從觀念切入先繞過那些我已經在演講、研討會聽過好幾百遍台灣人掛在嘴邊的大哉問(錢從哪裡來?如何說服政府推動相關政策?台灣代工產業會受到怎樣的衝擊?)──大部分屬實踐取向的問題,有些又與艱澀的經濟學相關(「你有算過拉弗曲線嗎?」)(註1)──任何一個問題,老實說,我都有些難以招架,好險我可以請出Guy Standing(2018)和Van Parijs(2017)兩位大師出面。他們兩位有關UBI的著作都在近期於台灣翻譯出版,皆詳細提出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層面實踐UBI的看法,看來只缺乏台灣在地脈絡了。但事實上,台灣也有學者做過研究,台大社工系教授古允文在2014年也即接受國發會計劃,提出相當詳盡的UBI研究報告(註2),我們可以從這份報告看到政府很早即對UBI抱持過好奇與興��趣。
這些研究成果已算是很仔細地回應了台灣人會好奇的一些上述有關UBI的實踐取向問題,本文限於篇幅不會再冗長地進行文獻回顧以及重新說明「UBI是甚麼」。我在意的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但很多人好像都忘記問了,那就是,在台灣這樣一個民主社會,我們若要依循民主途徑,在獲得廣泛民間共識下依循體制內路徑(譬如全民公投)推動UBI政策的話,我們首先該注意甚麼?難道不是要先理解台灣人民對UBI這東西到底怎麼想的嗎?
台灣人到底怎麼想UBI的-誰是UBI的支持者?
我們可以從2017年底一項中研院的量化訪談研究(林宗弘2017)啟程,林宗弘在這篇研究中,透過隨機電話訪談的研究方法獲取台灣人民對於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看法,結論最後顯示為:
「統計分析顯示,雇主與高教育程度者──勞動市場上的優勢中產階級,相對比較反對全民基本收入...高教育程度者仍相當支持提高最低工資,高教育與高收入者皆支持同性戀權益,但是兩者都不太支持全民基本收入。這個結果並不令人吃驚,畢竟雇主與高社會經濟地位者比較擔心提高稅收負擔...」(林宗弘 2017:141)
我們可以從本段文字見到,量化研究的結果顯示,反對UBI者以「勞動市場上的優勢中產階級」為主,而林宗弘認為中產階級的主要反對原因是稅收負擔問題導致。至於林宗弘討論到支持者時,則說明:
「...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支持提高最低工資者,也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左派確實較支持全民基本收入,這些台灣民眾也會傾向支持同性戀權益,然而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者卻主要是邊緣化的勞工,可能是男性、低教育程度的基層勞工或失業者,或是非勞動人口如退休領年金者。」(林宗弘 2017:142)
這段文字則顯示,UBI的支持者主要以「邊緣化的勞工,可能是男性、低教育程度的基層勞工或失業者,或是非勞動人口如退休領年金者」為主。
這樣的結果,也相當程度符合林宗弘採取政治社會學的「權力資源理論」,進而事先預想這項政策對於社經地位不同的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利益衝突的猜測──由於無條件基本收入實施後將可能顯著提高中產階級的稅收,使得反對者以新中產階級為主;而對於處在市場邊緣的弱勢群體,則不需面對稅收上的相對財富剝奪,所以支持者以這些群體為主。一切結果也似乎相當合乎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人們會基於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最佳政治抉擇。然而,這篇文章將以我個人在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組織參與觀察、訪談的經驗,提供��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重新思辯無條件基本收入支持與反對的相關議題,拓展這方面的討論。
在UBITaiwan內部的支持者們,有大部分會員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碩士生,甚至有年輕科技新貴(見圖四、五),顯然與林宗弘對於無條件基本收入支持者的研究結果有所出入,同時以筆者自身參與無條件基本收入演講的經驗,也觀察到席上有
醫生、設計師、新創企業老闆、科技工程師等(註3)(見圖六、七),因此他們為何會好奇無條件基本收入,甚至加入推廣這項政策,成為耐人尋味的現象。從「權力資源理論」或者「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出發,他們實在沒有太大的理由、誘因參加這麼一個辛苦又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但需要無酬籌備一堆活動,還會被人指責整天好吃懶做只想要政府給錢。

圖四:UBI Taiwan會員大合照。

圖五:UBI Taiwan會員日常會議討論照片。

圖六:2018年底舉辦的UBI講座。

圖七:參與民眾有醫師、設計師、新創企業家。
所以我將透過針對這些會員的訪談,試著提供人們不同層面的省思,一如過往人類學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彌補那些量化研究中難以挖掘的質性面向,呈現出看起來更像是生活中我們會在捷運巧遇的人類臉譜。
在2018年春天,我分別訪談了八位UBI Taiwan的成員,詢問他們的支持原因以及生命史,探案他們各自支持這項計畫的理由。而在林宗弘的調查結果出爐後,更使我好奇這些看起來相對是不愁吃穿的人們為何會加入?
酥酥是一位科技新貴,台大資工所畢業,看起來實在不像是會支持UBI的社會底層人士,甚至UBI實施後,他可能還��需要繳更多的稅。所以我就好奇發問了:
我:你身為高薪的資工工程師為什麼還會想要推無條件基本收入呢?
酥酥:恩...我雖然現在是資工工程師,但不會認為自己比較厲害之類的。我在工作時,有看到公司裡一些打掃阿姨,聽他們抱怨工作的事情,心裡就想說我們的差別是甚麼,然後他們的薪水那麼少。我這幾年覺得我只是比較幸運,並非我聰明,只是我生對時代,剛好對資工有興趣,而社會又對資工有需求,以前我也不知道資工會那麼吃香。不過掃地阿姨是一件事,又加上我剛好認識到UBI,讓我思考UBI可能是一個可能。但現在的主要原因是,我認為生為人不應該只是這樣。
所以酥酥是抱著一種對於陌生人的關懷,期待讓打掃阿姨或者其他工作者──只要是人類,都能夠享受到生命真正的意義。其實這正呼應了Ferguson(2015)所好奇的,當代人們是否還存有那種不求回報的分享,或者是利他的「社會性」──因為認知到彼此共處同一社群而互相關照,人們對於社會財產的分派方式因此不會再侷限於私有財產制,而將願意適度地分享。
這又可見於我與成員傳翔的討論,此訪談段落前,他告訴我他可以輕鬆過上他想追求的理想生活,譬如去咖啡店或書店當個文青店員,過上簡單生活,成為小確幸最佳代言人,即便UBI沒有實踐��也沒關係,於是我又好奇了:
我:既然現在就可以達到你理想的生活了,為什麼還要推動UBI呢?
傳翔:我覺得以我現階段的能力而言,我只是單純希望讓我周遭的、我喜歡的朋友們可以過得更好更快樂,因為我看到身邊很多朋友為了準備考公職而過得非常痛苦、不快樂,所以我想要推動UBI。我不敢說我自己是為了台灣、為了全社會。
傳祥的理念恐怕更貼近大眾,他單純期待讓身邊朋友過得更好。
從上述的言論出發, 我想特別強調, 在討 論 UBI 的支持者時, 我們實在不能忽略社 群紐帶,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聯繫, 這 不是「權力資源理論」隱含的「理性經濟 人」預設下所能涵蓋的, 而是一種共同存 有的狀態, 人們可能基於「社會性」, 基 於對他者的關懷而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 概念。 但最後, 我要鄭重強調我沒有徹底 否定「權力資源理論」這一套方法論的意 圖;這種推測也確實掌握了社會的「部分 真實」, 我只是想與林宗弘共同合作, 各 自貼上自己看到的一片拼圖, 拼湊出血肉 更加豐富的 UBI 支持者圖像。
台灣人到底怎麼想UBI的-誰是UBI的反對者?
如果要承接林宗弘的量化研究,提供一個更加清晰的反對者圖像,也就是尋找那些反對的「中產階級」,思考他們到底是誰,是怎樣的人,究竟該如何做到呢?我在2018年的春天,恰好就在臉書上遭遇了這樣相當符合林宗弘描述的反對者,年齡約三十五歲上下,月收入也相當高的白領階級工作者,經濟學系畢業。因為他批評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臉書貼文被轉發至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相關社團,激起底下UBI支持者的批判聲浪,因此我才輕易尋找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反對者,而後立刻鼓起勇氣向這位反對者約訪。也許因為誠意,意外獲得他理性又認真地回應。儘管最終難以現實中約訪,最後他以書面回應的方式回答我的訪談問題。簡言之,他對台灣美好社會的想像在於「產業多元性」、「工作機會增加」、「經濟發展」等幾個關鍵詞彙。且讓我們暫時記住這些詞彙,先前往下一篇訪談。
廷耀身為經濟系的碩班學生,向我口齒伶俐地講述他自己熱衷於UBI的反骨經濟系男孩紀實:
我在經濟系,只要一開口講到UBI,所有人都唾棄我。我跟系主任講UBI,他氣到摔門出去,認為我經濟學原理沒學好,但我是我們班書卷獎,碩士畢業。我還跟幾個腦筋轉比較快的朋友講UBI,他們都不支持。後來我跟另外一個老師討論UBI做研究,換我氣到摔門出去,對方是勞動經濟的大咖老師。然後我們再也不講話。因為我當時問他如何解決未來社會低端人口被AI淘汰找不到工作的問題,他回答「再教育阿」、「再投入職場阿」。我回答難道你嫌我們教育還不夠多是嗎?那不然大學念個二十年?他就也暴怒了。我自己認為教育也沒辦法改善多少這樣的問題。
廷耀的訪談顯示經濟系老師反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理由,在於其認為問題根源在於「加強人力資本素質」,而這也成為廷耀與老師爭辯的衝突來源。
Ferguson(2015)的批判。他在南非針對基本收入做研究,並指出政府與人民普遍存在著「生產導向」的思維,甚至在學術界,從馬克思以來就存在著強烈的「勞動主義」,強調工作是人們生活的美德(註4),因此大部分的政策都圍繞在「生產」環節打轉,大部分消除貧窮的政策都以提供福利服務、建造公共設施、勞動教育等為主,唯獨害怕直接給付現金,對於現金是否能解決貧窮問題的抱持著懷疑和恐懼。
我們也可以從以上兩個對於反對者的訪談和側記中見到,他們的觀點也著重於「生產導向」,強調「產業」、「勞動」、「人力資本」等概念的重要性。但是Ferguson(2015)強調人們應該將焦點從「生產」,轉移到「分配」這個經常被忽視的經濟環節之上。「生產」導向的思維,不僅使得政府無視全球化過程下國際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均,仍把政策重點天真地放在國內就業措施而非正視社會結構性問題;也如Van Praijs(2017)所批判的,生產導向已經造就太多環境汙染;而且打從二戰後期全世界的經濟就高速起飛,全世界的財富連年暴漲,我們迎接著人類歷史上最富裕的社會,然而時至今日,人類終究還是無法解決失業貧窮問題,甚至還有越趨嚴峻的可能,無疑是莫大的諷刺。因此Ferguson(2015)特別指出不管是政治或者學術領域,都應該重新思考「分配」作為一項通往正義的道路,或者作為嚴肅的學術議題討論。
Ferguson(2015)蹲點研究的南非,恐怕還是會被讀者嫌棄離台灣太過遙遠,那麼李宗榮和林宗弘(2017)近期的社會分析,恐怕將成為一記更有力的還擊,他們以經濟社會學出發,指出台灣1990年代後向新自由主義國家轉型的種種社會結構性問題,揭露出台灣如何從過去發展型國家的「奇蹟典範」轉向目前陷入瓶頸的「衰退典範」;這包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越來越小,過去「國家主導產業發展」的政策模式已經失靈,同時兩岸開放政策也使得台灣中小企業面臨艱鉅的競爭挑戰,再加上種種國家邁向金融化、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全球化的過程,使得台灣政府想要在當今複製過往產業發展型國家的成功越來越困難。看到這邊,我們會發現台灣所面臨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困境,並沒有與Ferguson所觀察到的南非現狀相差得太遠。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進程都把我們共同拋向不安定的風雨之中,越來越難以保證人們過著長期而穩定的「好生活」。於此刻,台灣人民若還將「好生活」的想像寄託在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上,以及還認為培育優秀「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手段,未免有些天真,並且忽略了上述所提及的結構性變遷。
結語-「好生活」之途何處尋?
在這篇文章裡,我藉著UBI�的議題辯論,貼緊台灣脈絡,旁敲側擊出每個人對於好生活各自相異的想像,我擴張了對於UBI支持者的討論,探詢一種連「中產階級」以上也願意在自身利益受到剝奪的情況下支持UBI的「利他社會性」,也回應了一些常見反對者論述的盲點。在動亂不休的社會之中,我認為他們唯一,也最珍貴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在盡可能地擴張他們內心所想像的,璀璨浪漫的「好生活」版圖,讓我們所共處的台灣在烏煙瘴氣的辯論之中,逐步迎接遙遠夢境中的的烏托邦。
*註解:
1 當我在看最近DavidGraeber的大作《狗屁工作》(2019)時,意外發現他諷刺經濟學家的高傲態度以及經濟學界術語如何主導學術討論的現象時,也舉出對方詢問拉弗曲線的例子。
2 請參考古允文(2014)。
3 當然我們不應預設這些人參與等於支持,但這些人在參與量的增加,顯示此趨勢仍值得我們注意。
4 其實最近DavidGraeber(2019)在他的《狗屁工作》一書對對工作美德的源起有著更詳盡的歷史爬梳以及分析,但並非本文重點而未考慮放入。
參考資料
古允文
2014 《我國社會福利體系中之基本所得保障研究》。��國象發展委員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政策學會。
李宗榮、林宗弘
2017 《「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刊於《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清興社會》。李宗榮興林宗弘編,頁2-43。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林宗弘
2017 《台灣民眾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思想》34:127-146。
David Graeber
2019〔2018〕 《40%的工作沒意義,爲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Bullshit Jobs: A Theory)。李屹 譯。台北:商周。
Ferguson, James
2015 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uy Standing
2018〔2017〕 《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從基本收入出發,反思個人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以及如何讓社會邁向擁有實質正義、自由與安全感的未來》(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Happen)。陳儀譯。台北:臉譜。
Van Parijs Philippe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2017〔2017〕 《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許瑞宋譯。台北: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