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學的最佳理解者
野林厚志 |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陳佳盈 初譯
黃智慧 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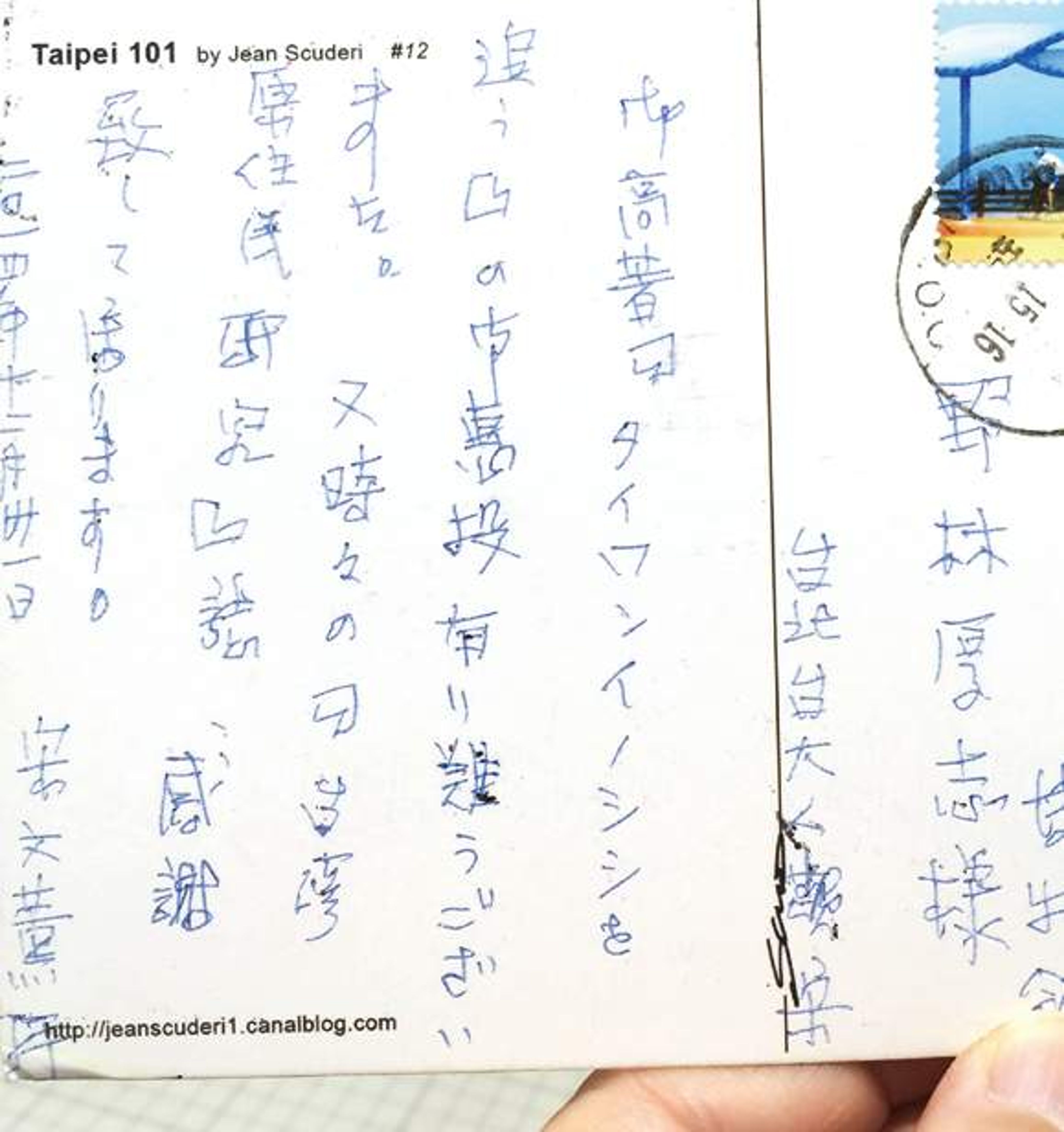
我生於1967年,和我同輩的日本學者中,曾和宋文薰先生說過話的人應該不多吧。雖然一部分是因為年齡的因素,主要還是因為在臺灣從事考古學調查及研究的機會對日本學者來說相當少,而且研究臺灣人類學、考古學的學生人數也很少的關係。不論如何,能和宋先生談論許多話題、互通信件,對我而言是十分感動的事,也是我的驕傲。
說到宋先生,總是穿著吊帶褲,一手拿著啤酒,一手不是插在口袋裡就是拿著菸,這個造型經常成為話題,但是對於當年專攻民族考古學研究,還是學生的我來說,宋先生是學問上的知音,也是��臺灣的老師,更是我的恩人。
當年我選擇以達悟族的根莖農作之工作小屋的機能與形態,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帶著田野調查的資料拜訪了宋教授的研究室。前一年拜訪連照美老師,她已經介紹宋先生給我認識,因為還沒有任何田野調查的資料,還是個分不清東西南北的學生,抓不到重點地向宋先生說明了自己的研究計畫。宋先生聽完後莞爾一笑,從冰箱裡拿出臺灣啤酒邀我一起喝,然後閒聊了一些不重要的話題,就結束了那一次的會面。
再次拜訪宋先生時,我以為也只是打個招呼喝個啤酒而已吧。但我向宋先生說明了田野調查得到的資料,並將自己想研究的事情,也就是投入的勞動量和栽種的薯類、和聚落的距離會對搭建的工作小屋的機能及形態產生何種影響等課題敘述了一遍之後,宋先生回答說,「你想做的事情,是和國分教授有點不一樣的民族考古學呢,是屬於Ethno-archaeology吧!」這件事至今仍深深留在我記憶之中。宋先生還告訴我,臺灣的考古學中尚未被調查的課題,包括過去原住民居住地區的研究與發掘調查。在探討歷史的連續性時,了解居住環境和考古學遺址間的關係十分重要,但是進入山中的調查和發掘十分辛苦,所以很少有研究者願意投入。後來,原住民族間對於傳統領域的關心逐漸增強,過去的居住地區調查也有大幅前進,可見宋先生的問題意識相當具有前瞻性。
宋先生看到我將日治時代製作的地圖放大影印,拼湊貼成地圖來標示工作小屋的位置,便說這樣一定看不出來土地傾斜的情況,於是將我調查的地方的地形圖拿出來,並給我描圖紙,只說了句:「描繪等高線吧,這是基本學問。」然後就離開到隔壁的房間去了。留下我,埋頭拼命地描繪等高線......。
收到訃聞後,向臺灣的友人詢問了喪禮的情況,一面著手寫這篇文章,益發覺得真希望能從宋先生身上接受更多的引導,學到更多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