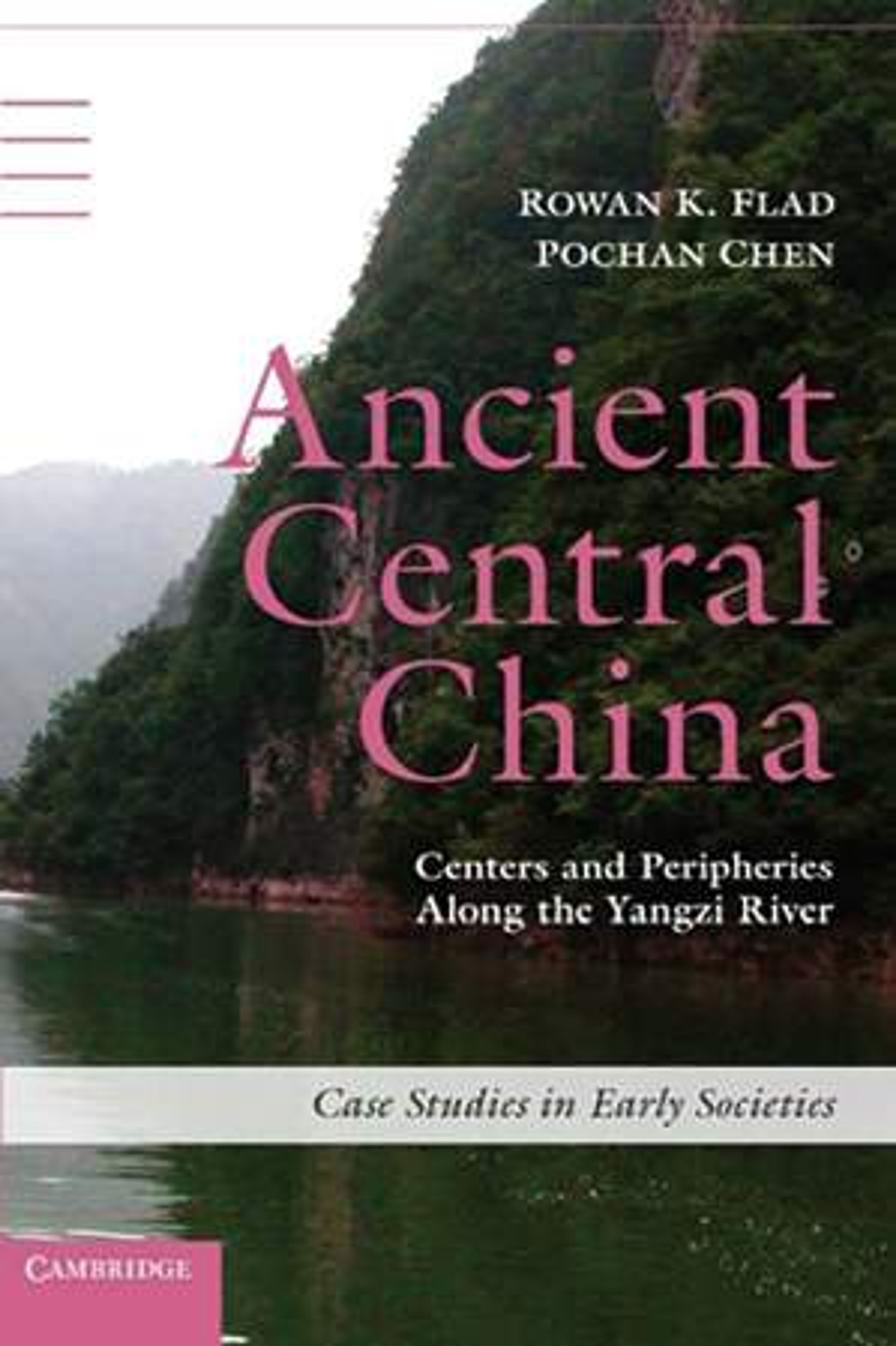比樣、謎樣、好樣 — 不一樣的伯楨學問
謝世忠|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前言
這幾年,一直注意到陳伯楨教授的學術表現,越看越神奇,總覺有不與人同的特殊之處。筆者之所以敏感於此,並不只感受到他學士班時曾是我授課的學生,從而喜悅於青出於藍的美好,更因伯楨的研究與想像中自己的「拿手」絕活,似有相連,卻不知從何說起。先是幾年前筆者曾主持伯楨在人類學系作的一場演講,他一開口就搬出東晉人常璩所撰《華陽國志》一書(完成於公元348-354年間),聞之甚感訝異,應是說又驚又喜。原早以為不可能從人類學同事中聽到談論該書,如今卻彷彿獲有知音之感。按,常書是描寫中國西南地區本土人文最早的專書之一,過去碩士論文研究川南滇北的儸儸族(今中國統稱彝族)民族史,指導教授芮逸夫院士就要求必須細讀該著,不得偷懶。問題是,伯楨作為一名考古學者,辛苦唸這本古書幹嘛呀!對他的好奇自此起始。
本文題目首詞「比樣」,就是“beyond”。Beyond什麼?“Beyond commonly recognized archaeology”,亦即超越一般所認知的考古學。伯楨的學術旨趣與操作方式,真的與傳統史前考古風格有所不同,一直很想好好請教他造就今天的來龍去脈,卻因伯楨見到我就是老師好老師長老師短的,非常禮貌,害我忙著享受恭維之際,忘卻良機。比樣就此成了「謎樣」。故事之所以變為謎樣,不僅僅是自己準備提問者,主角不克回答了,主要是臺大人類學系和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如何秘方教出這樣謎般的學生,從古文獻到遺址發掘到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到統計技術再到體質人類學,萬般皆備,筆者也很想了解。陳伯楨博士短短10年的大學教師生涯,即能建置自身的全方位學養技藝,一個詞形容,就是「好樣」!
今天這篇文章,筆者與伯楨師生同事打屁四分一世紀,以一個非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家,寫寫一位兼具比樣、謎樣、好樣特質之不一樣的考古學家,心情也喜也悲。不過,看在「比」樣、「謎」樣、「好」樣,「比謎好」,就是「比me好」(比我好)之意的學生成就份上,當然打起精神,拿起常在會議桌上借伯楨簽名報到的綠綠鋼筆,開始書寫。
話說古文三人組
前節提及《華陽國志》,可以唸之用之,好像很厲害了。然而,這只是小小一片蛋糕。伯楨博士論文於開筆後不久處的第18頁,羅列如下準備在文內大家參引的古文獻,它們是:《周禮》、《左傳》、《國語》、《管子》、《說苑》、《史記》、《漢書》、《後漢書》等,而多數材料都早於《華陽國志》。另外,考古遺址出土的楚簡、秦簡、漢簡、漢帛書、以及印刻和鼎盤文字等也不在怕。看過伯楨包括博論在內的各個主要著作,的確諸��多先秦文獻都在他筆下充分運用,而且不是簡單貼進就罷,更有精闢討論。問題是,年輕輕陳伯楨的此一不少長輩和文史專業心儀的「國學」知識,到底何來?筆者過去除了芮老師逼讀之外,史語所高去尋院士教授「中國考古學專題討論」之時,也花不少時間介紹該等古書。但是,我二十多年臺大任教,課堂上從未片刻提到上古經典各著,因為當代人類學取向早已與芮高時代大異其趣。所以,伯楨的特長謝老師沒教,與我無關,相信他上過的其他人類學系課程,也無相關連結。那陳博士如何作到?為求解答,轉往美利堅詢問。
伯楨與加州大學同窗現任哈佛大學JohnE.Hudson考古學教授Rowan Flad(傅羅文)的長年兄弟情誼和學術夥伴關係,你我皆知,也羨煞多人。他倆合作2013年由劍橋出版的Ancient Central China:Centers and Peripheries along the Yangzi River(古代的中國中部:長江流域的中心與邊陲)一書,堪稱張光直1963年初版流芳近半世紀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之後的中國考古第二經典。裡頭和伯楨博士論文的方法旨趣一樣,就是大量先秦文獻入列引論。傅羅文告訴筆者,他和伯楨最感驕傲的即是該書參考超過一千份古今相關文獻,應該沒有漏掉任一該找而未找的書冊,於是書目部分就幾乎占了全書四分一的頁數,其間伯楨的努力極具貢獻。這當然很棒,但是,問題還是在,誰傳授古文功夫啊?
筆者專問羅文此事。他先答曰哥倆曾修過恩師Professor Lot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所授的專唸古典中文(classic Chinese)課程,還曾大家一起讀了一長篇王國維的文章。他又說,伯楨對歷史小說知之甚詳,尤其是三國人物,田野期間每每聽他講故事。不過,他越說,謎團越在。筆者續問之:「不對啊!羅文兄所提之古書如三國小說等等並不那麼古耶!而王國維根本是近代人嘛!事實上伯楨在學術上討論的是早於三國千年的商周時代哩!而且先秦古文比歷史小說類的不那麼古文,困難好幾倍喔!」他回說,或許伯楨上過David Schaberg(UCLA先秦文獻《左傳》與《國語》研究專家)和Richard Gunde(UCLA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專家)或其他教授的相關課程,但,最重要的應是這位年輕人的高度興趣與熱忱,才促成陳博士畢業論文以及二人合作新書各個古文論述章節能夠精彩有力。羅文說,青銅器銘文和遺址出土竹簡解讀困難,伯楨也幫了忙。
問完了同學,問老師。兄弟檔的大著首頁題字獻給了業師羅泰,可見後者對於前者的關鍵影響。我問羅泰教授,伯楨古中文知識何來?他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羅泰指出,伯楨的確有修過他所授如何將古典書籍資料納入考古出土分析的課程,但,學生在閱讀古文上原本就毫無問題。他認為,其實伯楨不需修習任何中文古籍的課,即能應用自如。羅泰覺得應是伯楨的中學教育學習成功,中文底子優良。羅泰和傅羅文都表達了看法,亟欲尋找的問題稍有眉目。不過,有些問題其實也不需一定問到底,至少我們得知伯楨有天賦有基礎,再加上加州大學的充足師資,尤其羅泰羅文伯楨三人的古文重視,一起研究討論,才能成就非凡。伯楨幾次笑笑談起,當年中文典籍課上,就三人參與,羅泰教授好像總是舒服瞌睡,讓學生自由講,唯每當少年仔開始胡扯了,老師必定驚醒止住亂說。玩笑歸玩笑,想像場景,古文三人組正在合作無間,儲備了驚人的後續學術展現能量。
變成找鹽三人組
當然,這三人不會只以讀古書當最終目的,他們有其考古學的學術目標,那就是,鹽的考古或說鹽業考古學。老師和學生都對鹽感興趣,伯楨加大碩士論文書寫南島語族起源的課題,為何轉到中國鹽的考古,而且一作10年不停,來日還得再多探問羅傅二位學者。
長江中游的鹽鹵是一重點,但,伯楨他們也注意到海邊鹽業的出現情況,並認為岸邊海鹽和內陸鹽脈會因政治經濟的變動而彼此消長。甚至山西或更北方的井鹽情況也多次見諸於三人的文字。總之,師生三人礦鹽、海鹽、井鹽都在行,古文三人組,此時轉為找鹽三人組。「當時應該有產鹽了」、「這個遺址主人生活或許有鹽」、「會不會已知用鹽了」等等詞語,穿插出現於伯楨文論中。可見,多年來,他念茲在茲就是鹽,而他的老師同學也不惶多讓。
伯楨:五反大將
伯楨用典讀書,可不是照本宣科照單全收,更非畏懼權威大師之輩。他每份經籍都有見地,對大量中國學者的考古鹽論,更是意見多多。筆者至少整理出伯楨如下的五點學術異觀。綜而看之,這位曾經教過的學生,簡直天生反骨。不過,好像1993-1994年「中國民族誌」必修課上還沒太發作,授課者謝老師雖不至於以為伯楨僅是一名謄筆記的乖孩子,但,也想像不到他的學術細胞竟如此飽滿,一下就可看出許許多多過往研究的問題。如今,年紀已然資深的筆者,其實是細讀他所有要作之後,對成材青年的重新認識。
反對古文霸凌
伯楨發現,中國史家太過珍惜極古的少少幾份典籍,於是縱使現在考古資料不斷湧現,多仍以出土物來比對古文獻。換句話說,文獻依是上位。伯楨的態度是,應以出土資料來校對文獻才較合理。此外,有些舊史材料,也不能因它的久遠,就自然具有代表性價值。例如,《後漢書》作者范曄係距所書寫之東漢已有二百多年的南朝人士,因此許多內容記載都需質疑,尤其伯楨的四川鹽產歷史考古學與漢代息息相關,更讓他謹慎小心,絕不如傳統史家常見著有盡信書之嫌。
反對唯陶器論
很多遺址都出現大量陶器,當然容易引起研究者關注。但,關注是一回事,卻不宜就以此為唯一。伯楨認為,必須全盤或全方位的看待遺址出土,現在的問題就是,數量較少的物品往往受到忽略,因此,研究結論即直接導往偏差的解釋方向。他和夥伴專研的四川盆地,無論是博論時期的東面所謂峽江地區(包括重慶至三峽),還是近幾年陸續開發的西面成都平原,剛好都有巨量粗製陶器出土現象,伯楨一直提醒不宜將相關年代假設太早期,因為只當成生產工具用了即扔的燒鹵水取鹽容器,基本上不須講求裝飾精緻。所以,相當晚期或甚至進入歷史時期很久之時,都極可能粗造品續出。
反對文化史盲
考古學者很喜歡建置考古學文化。出土幾個遺址之後,立即興起歸類成群或劃為同一,再與他群區辨分出上下左右關聯。也就是說,一個個文化出現後,學者很願為它們排出年代序列,如此,一個區域的史前文化史赫然成型。當然,學人如林,一定是你排你的,我列我的,於是,幾種文化史論舊並陳於圈內討論中。但,伯楨以為,這不應是考古學的最終目的,更何況,大家紛紛以看到的類似器形花紋色彩來統歸我類,但,若細究之,則常常看似同類卻差距甚大,而這些極易被忽視。盲目的只在建立文化史,其實不甚理想,偏偏四川考古圈圈很喜歡作此檔兒事。
反對人必有鹽
「鹽是人生活必需品」,此語不假,但是,它是在今日不假,因為已成了健康維生的普通常識。至於在古代,則不能通通以此認帳。但是,偏偏諸多學者都自動地以當代的鹽觀來解釋千多年前的人類歷史,舉凡出現鹽品,就認定由於生活必需,所以業已普化使用。然而,整個周代800年,一直至秦朝和漢朝初期,伯楨都認為鹽產其實有如象牙琥珀一類的奢侈象徵高調生活,只限貴族王公享有,尚未成為一般人日常用物。證據之一就是掌管鹽品者均是皇家官員,代表處理該物範圍僅及於上層社群。直到西漢武帝才明顯出現政府公務員收稅鹽巴的紀錄,亦即,民生用鹽普遍,大家繳納稅金,更利於統治效益。
反對總是征伐
歷史學家習慣於使用政治競爭或戰爭衝突的解釋,在伯楨感興趣的春秋戰國時期長江中游巴國與楚國關係課題上正是如此。然而,此一說明古代人類活動的方式,常見漏洞百出,伯楨在數種論著裡,表達了�他的批判。例如,史家們認定一向楚強巴弱,所以從二國邊境進入巴國內地二百公里鹽產處,竟然出土不只一座典型楚國墓葬,必是強國征伐取土和佔有資源的證據。但,伯楨認為,一方面鹽產是長期事業,不會一次征戰就了,更何況古時有交通限制問題,缺乏後勤補給的行軍,可以進展之途程不足一百公里,基本上到不了巴國產鹽地,還有楚墓周遭仍是巴國遺留為主,談不上征戰佔有的情況。因此,他推斷這幾個楚墓,很可能是楚國的鹽商,他們的資本和技術主持採鹽,而勞工則以巴國人民為主。
伯楨:我的主張
伯楨除了展現五反大將精神,更於反了之後,積極提出相對應的建設性觀點。他的學術主張至少也有五點:
考古出土講話
考古出土不斷湧現,這是不爭事實。因此,必須以這些物件作為完整的分析對象,從而建置考古學知識。鹽產的較大量出現,正好就與諸多先秦文獻存在的時代重疊,雖然仍需要充分閱讀參考,但,不宜始終以之為理解古代的標竿。除了帛書竹簡和銅器銘文之外,多數考古出土不見文字,研究者很可能順手地拿起文獻比對,然後遽下結論。問題是,二邊比不到者多,研究者萬不能因此降低了出土的價值。總之,考古遺址主人的生活,仍應以在地出土物所能說明者為要。
強調整體面向
如欲探討遺址主人生活,勢必要全面掌握出土遺物。像前節提及之只看到大量陶器,就忽略其他非陶類出土物,那麼,所得結論一定偏頗。認識乃至瞭解遺址主人社會生活是關鍵要務,然而,不少研究者捨此而往其他探索方向,導致史前或早階段歷史時期的社會史風貌,很難見著曙光。
關注物人關係
考古學文化與文化史序列的建立,主導了考古學者多年,迄今仍有人繼續努力於此。伯楨出身人類學系,自然會強調人所參與之物質世界如何與人形成互動關係的景況。倘若只在物品尤其是陶器的泛美學比較,然後互聯文化歸屬,繼而判定誰是文化史上的一期,哪一個又是二期,或者某某文化早期類型受到另外文化中期代表性特質的影響等等,那,永遠等不到物與人之間活生生關係的闡述機會。不過,有趣的是,伯楨在博士論文中提出他川東主要田野遺址出土製鹽陶器依技術發展計有8類,而縱使再三澄清其與四川考古家喜愛建立的考古學文化並不等同,卻也不得不每講一類,就必須稍稍提及它相當於某位學者主張之特定考古學文化時期。足見伯楨所面對者是強勁的在地主流學術。
鹽的上下變遷
伯楨對於鹽物與人的關係,始終以證據為基準來表達看法。人盡皆知鹽是最基本食材酌料,但,它不會憑空就成為人人日常必需的食品。鹽如何成為日常所需?以及成為日常用品之前,它又是如何存在?還有,誰在主導它的製造、銷路、運送、存放、與價值?凡此問題,都必須一一仔細探索釐清。伯楨的重要研究發現,就是鹽落在貴族階層手中至少好幾百年,那個時代根本無所謂鹽是日常必需品之事實。後來不論是海鹽抑或礦鹽、井鹽、池鹽,才慢慢出現官民類似聯手管理情況,最後終於成了平民百姓日常必需品,從而生產者繳稅國庫,鹽變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之一。鹽從上層所屬,轉而成了下層日常,其生命史代表著人類社會史的一環,伯楨論著直指要點。
鹽的世界體系
伯楨主張應跨越出總是以「國」為範圍的分析方式。他借用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經濟要素可以超出政治國度,也就是在經濟領銜目的之下,唯有以較大世界範疇角度觀看事情,才能掌握時代脈動。楚國政治勢力比巴國強,但,鹽產主要地區位於巴國境內,雙方不以征伐或被奴役作為鹽資源控有的策略,從而由鹽商資本的投入開採,以及在地提供勞力配合的方式,取得共利結果。所以,在政治力量上,楚國似是中心,而巴國屬於邊陲。但,此一中心邊陲絕對二分,並無法幫助我們精確了解大範圍世界運作的模式。反而,有時邊陲顯得張揚(如鹽產的豐富),引來各方羨慕眼光(鹽商紛紛投資參與)。
不一樣的伯楨學問
伯楨10年經營,一日當十日用,筆者作為他過去的授課教師,重讀學生豐沛的學術論著,獲益之外,情緒感受尤為深刻。以下為近日整理出的伯楨十大學問特色,越是了解他專研學術用心,越覺得這份學問實體的確很不一樣。
田野考古
中國考古學是人類學系老牌課程,但,田野考古始終與它無緣,長久以來,系上教授田野方法與實習,都只選在臺灣各地。伯楨可謂在中國土地上開挖第一鏟,亦即,實際至中國進行田野考古,一手資料獨家分析。原本未來應有充分機會將學生帶往實地調查,無料突然發生老師驟逝憾事,無疑是系方與學生的巨大損失。不過,伯楨留下10年中國經驗,在臺灣考古學史上已是一項紀錄,勢將產生重大影響。
講述出土
伯楨對於出土物所代表之意涵,總是細心咀嚼,然後提出合理的說法。例如,鹽產地區遺址出土大量提煉鹽結晶的尖底陶器,它到底如何使用,大家都關心,有極資深的學者認為就直接插入土中,接受陽光熱烤。但,伯楨端詳各項跡象之後,認為應是先備有一較大架盤結構,再將一個一個尖底器放置上頭,繼而燒煉鹵水取鹽,如此方能事半功倍,火力旺盛,更合於操作技術的原理。像此類與人不同解釋的提出,遍見於他的研究寫作中,也總能令人眼睛一亮。
解讀古書
伯楨對中國古典,包括最早典籍,均可讀可懂可考可判可用,不僅不落入食古不化,更且大力批判死抱不放或以此為唯理者。他是考古學家,其指導教授羅泰博士跟筆者說,原本研究先秦考古學或歷史考古課題,就非得充分參考古書不可,伯楨當然深知箇中道理。但是,中國多數學人也對上古史感興趣,他們當然知道考古出土接續湧現,無料卻總習於以幾本千年文獻為詮釋歷史的基準,新出土文物資料只是配角。相較之下,伯楨的古文解讀方式顯然更吸引人,有機會唸到其博士論文第三章,就可明白筆者所言不假。
統計技術
取得博士學位到臺大任教之後,伯楨的後續研究計畫,一直保持與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師長同學的合作,同時和中國學界的聯繫也極其密切,實可稱為標準的中美臺聯合學術事業。多份中英文研究報告和論文出版,也掛上三方的參與單位和成員名錄。出土遺物的統計處理及公式輸入與結果分析任務,常由伯楨擔綱。這份技術不是從臺大人類學系習得,他自有獲致功夫的辦法。系方聘得伯楨,學生受惠,因為自此有統計應用的課程可以選修了。
物文對話
遺址出土物與古文獻應有合理的對話策略。伯楨明白此一道理,因此,幾乎所有研究報告裡,均能有效地交參引用兩邊材料。歷史考古學研究方法告訴我們,出土物品與上古文獻需要並用處置,但,說來容易,作了知難。主要問題不是傳統考古學者只慣於分類陶片,描述物質用物,就是古書專家太過相信千古菁英祖先紀錄者的豐功偉業,因而輕忽常民生活的粗造品項。伯楨人類學系出身,知道庶民文化有著豐富底蘊,於是對於整體出土的觀察分析,私毫不放鬆,而對古早文書則謹慎以對。
理論充沛
前提伯楨討論巴楚關係時,引用世界體系理論予以解釋。然他並不是就直接套用, 而是先行細細檢視種種支持或反對 Immanuel Wallerstein 原初論點的相關文獻,之後再順暢行文以此嶄新認識公元前五百年時的長江中游政治經濟世界。伯楨展現出了基礎社會科學學問訓練的扎實,考古學者如此風貌,至少在中國和臺灣學史上應是前無古人。
中英西文
一般而言,作為一名學者,總是期望自己的研究發現發明,可以經由多重文字傳送,以使知識精華得以嘉惠更多讀者。伯楨的研究成果至少曾出現有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等三種文字出版品。一篇學術論文倘使有人願意翻譯成原作者所陌生的另種文字,不論動機目的為何,該文很可能本身就極具價值。伯楨10年的學術造詣,已然吸引跨國學人的注意,於是作品以多種文字呈現,留下學界佳話。
文化理解
傅羅文教授告訴筆者, Ancient Central China一書, 伯楨在第九章墓葬分析付出心力最大。而通看全書,最具人類學文化分析意涵的部分,就是該章。這下筆者就也點翹尾巴了。因為,對於伯楨的此一拿手,人類學系教學顯然有一定貢獻。還有,事實上,絕大部分伯楨對中國考古學研究情況的批評,都是基於學者們書寫報告, 老是缺乏社會文化生活說明之故。社會文化不成為重點,深度就不易顯現,伯楨深知道理, 於是乎其各項研究成果,就多具饒富�趣味的可讀性。
中外比較
欲對長江中游鹽產考古進行研究,可不是簡單事。伯楨為了建立自己雄厚基礎,花了不少功夫於中國全境製鹽情況的探討,以及世界各地鹽業考古的材料收集消化。有了廣泛之交參比較性知識的掌握,世界製鹽縱向橫向課題,都為伯楨所關注。閱讀他的相關論著, 還真能感受到古今世界人類為求鹽產順暢,總不介意建造出自我生活圈的鹹瘩瘩景象。
國際團隊
筆者直覺,伯楨與其加大師長同學長期合作,好作品不斷問世,引來一雙雙敬佩欣賞的眼光,而此一現象實可解讀為係自1970年代張光直教授主持濁大計畫以來的第二次臺美考古聯合研究佳話。只是PCC(Pochan Chen) 團隊重點中國,而KCC(Kuang-chih Chang) 團隊臺灣為主。陳伯楨的田野中國,彌補了張光直的紙上中國考古學半世紀缺縫, 而他和傅羅文的合作出版,更展現後經典「比樣」前經典的氣 勢。 傅陳 (Flad-Chen) 國際團隊的威力的確引人入勝。
結語
為了寫這篇文章,整個暑假滿腦都是伯楨身影。要為伯楨學術寫寫東西之原初想法起於臺北,不過,不久就開始苦瓜臉於澳大利亞阿德雷德 (Adelaide) 慢跑公園,續轉至美國西雅圖優雅海岸來回跺腳步, 接著飛到韓國釜山新羅王國舊地終於開筆,最終又回臺北結束任務。老師苦讀學生10年精彩,果有一番滋味。雖是討論伯楨學術貢獻�,卻不太想將文章結構成引文參考註釋繁多的制式模樣,一意就期望平鋪直敘一氣呵成,效果多少,尚待確認。不過,至少撰寫過程學習特多,真格而地感謝伯楨比樣、謎樣、好樣的留世珍貴。
時間會繼續流逝,有日伯楨學問終將成為古典。而古典的經典性,又會引來一批學術中人開始閱讀品嘗,然後就如往日伯楨眉批中國先秦籍書和當代考古論文般,這些新生代從中發現樂趣,激出創見。考古學、中國考古學、長江中游考古學、四川考古學、以及令人津津樂道的鹽業考古學,就此一直傳承壯大。無數世代之間,陳伯楨教授/Dr. Pochan Chen 名字必是此起彼落大家談論。或許不少學人同樣會認為伯楨學問很不一樣,很好,很謎,很比樣 archaeology。畢竟,伯楨推進了學術跨越行動, 我很有感,於是亟願加入他的粉絲團,共同禮讚這位年輕有為的考古/人類/史學家。
作者按:本文正式動筆為2015 年9月3日,完成於12日,一共 10天。惟若從引發思緒起算,則將近二個月,這期間還特意跑至留下不少歷史石刻真跡的韓國釜山海邊尋求靈感。文章寫就的目的係為紀念陳伯楨教授的英年猝逝,當時心情太過低落,才需遠方遊水,看看能否靜心下筆。初稿已於草成之後二星期(9月25日) 在臺大文學院演講廳追思會上宣讀。今天,傷心事過了周年,特將該文刊載於此,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