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他們是這樣的教我們
張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筆者1974年進入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大一的「人類學導論」是由唐美君教授教導,唐老師的專門領域是中國漢人家族研究。大二的「文化人類學」由陳奇祿教授教導,陳老師的專長是藝術人類學與台灣原住民研究,學期中間因為陳奇祿老師擔任政府官員,而由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台的尹建中先生代課,尹老師的專長是移民與人口研究。大二時還有連照美教授的「體質人類學」。大三文化田野實習課程是由洪秀桂與曾振名兩位老師帶隊到台東卑南族南王村落,洪老師研究過埔里巴宰族,師丈在政治大學教書,兩人好像都是留學法國。曾老師當時尚未從事客家研究。大三還修了李亦園教授的「原始宗教」、「東南亞民族誌」等課程。「原始宗教」與當時故宮博物院館長李霖燦教授開的「原始藝術」課程,是當時文學院最受歡迎的兩門課程,學生人數超過百人。李老師選用了在美國Rice university任教的Edward Norbeck撰寫的Religion in Human Life: Anthropological Views為教科書。全書僅有74頁,由系上翻印出售。李老師將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依照��黑巫術、白巫術、薩滿、占卜、等不同議題,每週輔以不同講義展開,都是老師講課,課中鼓勵學生發問或分組討論,算是非常活撥的講課老師之一了。
大四修了石磊教授的政治人類學,杜而未教授的民俗學。石磊教授因為其父親為考古學大師石璋如,而聞名系上。杜而未教授留學德國,學習文化傳播學派,是系裡少數留德教授,他所創的「月亮神話(傳播論)」相對於「太陽神話(傳播論)」在學界很有名。只要是系上教授開的課程幾乎都選修了,另外,還到歷史系修祿耀東教授的飲食文化史的課程,旁聽社會系葉啟政教授的社會學課程。
上述這些位人類系老師們,上課方式是以一本英文教科書為主軸,加上自己的演繹與舉例,例如人類學導論是用Marvin Harris撰寫的Culture, Man and Nature為教科書。文化人類學當年是以R. Keesing的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一書為教科書。當時尚無中譯本,因此大家都是原汁原味的讀英文專有名詞或田野案例。當時台北尚無出版社願意出版人類系的教科書,因為銷售量太小了。學生也無能力直接訂購美國的教科書。因此,人類系上有一個小小出版經費,可以委託羅斯福路上的雙葉書局或中山北路上的敦煌書局代為印刷裝訂這些英文教科書,在系上限量販賣給修課學生。這些即是所謂的盜版書。後來系上畢業的陳隆昊先生便是因應當時出版界需求開設了唐山書局,專門出版或經銷台大各科系所需之英文教科書。一直到現在還是羅斯福路上專業的書局之一。

李亦園教授與當年開的「原始宗教」課程大綱(局部)。(圖片提供/張珣課程大綱提供/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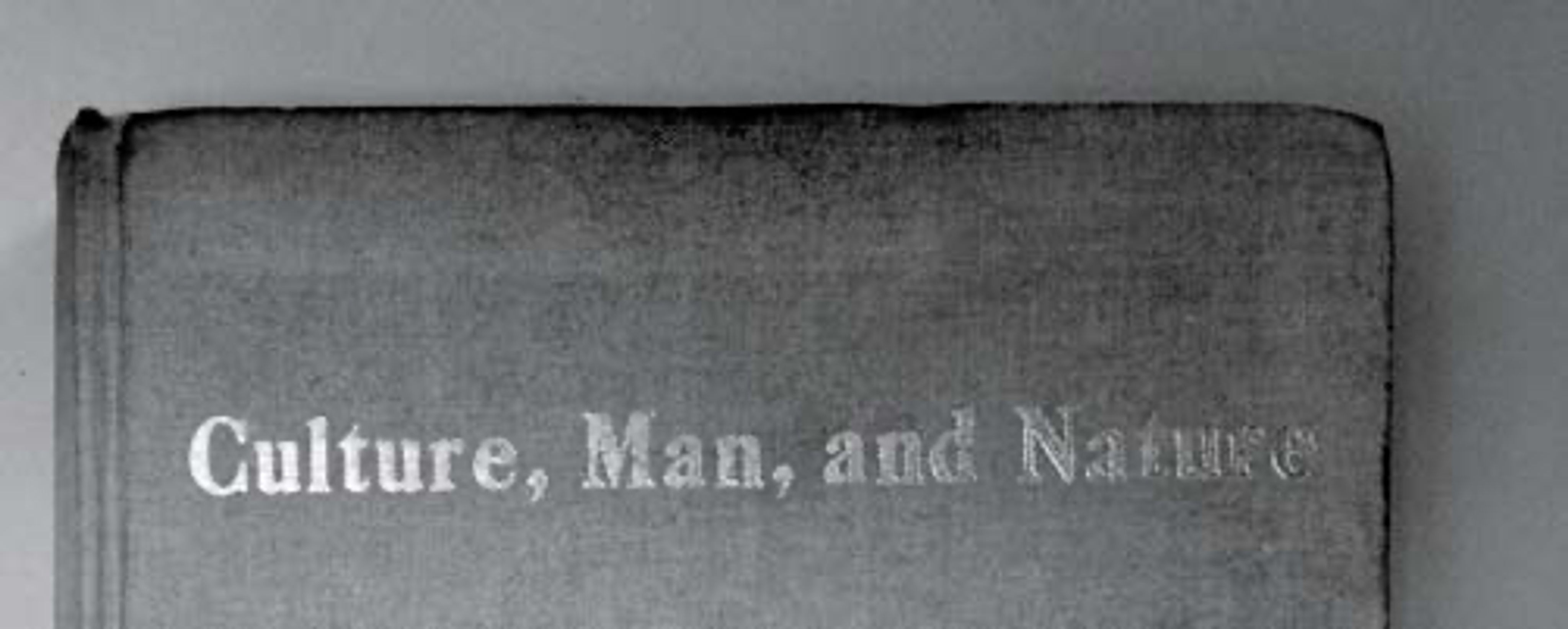
使用一本英文教科書的好處是根據英文作者一家之言,一人之說,完整而前後連貫。對於該門課程有一個整體的認識與學習。一學期下來十多堂課之間,前後有一個貫穿的主軸式理解與知識。有的課程不是使用一本英文教科書,而是授課老師在一學期當中不定期地分發數份中文或英文講義,學生們自己裝訂成一本講義冊。這樣的講課方式,不同作者不同主題的講義之間,可能缺乏一個可以前後貫穿的主軸,好處則是比較多元而廣泛地接觸不同派別與作者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當時一學期要閱讀的頁數與現在無法相比。現在是知識爆炸時期,每個人囫圇吞棗,每天塞進很多資訊。當時因為英文課本或講義得來不易,字字珠璣,每一個字都會咀嚼再三,反覆推敲,尤其是經典著作,更是一再翻讀。
到了筆者考上研究所碩士班的時期,李亦園教授教的「中國社會」課程,每週均給兩篇中文或英文文章,要求學生每週針對兩篇文章做口頭報告。當時有學生認為這門課程比較像是資料選讀,而不是授課教師有一家之言之後的演講課程。每週根據不同主題有不同講義,一學期下來,認識許多漢學家的研究成果或民族誌,但是何謂「中國社會」則無一定論。這門課在當時是社會科學眾多學科之中,唯一專門討論中國社會文化的課程,因此,修課學生涵蓋法律、政治、社會、經濟、人類學等學科,可以說是熱門課程。
在碩士班有芮逸夫教授開的「中國民族志」,黃士強教授開的「中國考古學」。上芮先生的課很有趣,每週上完芮先生會帶我們到他的住家溫州街附近,「老爺飯店」是一棟日式住家建築,老闆就在住家內開餐廳,僅提供一道食物,就是整隻的水煮「童子雞」。香甜不油膩,滑嫩而容易入口。王道還學長因為從醫學院轉到人類學,他每次最快吃完,而且將雞骨頭完整解剖,雞肉完全進食乾淨。其他同學都狼狽地將一隻雞切割得不堪入目。黃士強先生有一晚來搭救我們幾個研究生(王道還、蔣斌、林開世、汪珍宜)。因為我們在三樓研究生室聊天到天黑,負責鎖門的工友老魏完全不知我們的存在。等我們要回家才發現被鎖在洞洞館內,鄰近無人經過,無法搭救。每一間研究室都被我們嘗試打開,最後是打電話聯繫到黃士強先生。黃先生帶麵包與鑰匙來解救我們。主要因為當年沒有手機這種產品。
在人類系來說,英文閱讀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為人類學是舶來品,幾乎重要的理論或民族誌都是洋文作品。無形中,英文成為人類學家養成訓練中的重要工具,多數學生都在大��學時代死啃硬啃原文書,用盡各種方法來揣摩、體會、想像世界各地人類學家所描繪的地方文化。由於當年人類系在台灣是「僅此一家,別無分店」,每年畢業學長人數不多,也很少人會去翻譯洋文人類學作品,從來都是認命地死讀英文,沒有中譯本可以找。因禍得福,我們的英文程度在畢業時也都增強了,進入研究所之後,讀英文教科書不再是苦差事,反而感覺讀英文可以得到真實內容,偶而看到中譯書,總覺得隔靴搔癢,中譯文很彆扭,表達不出洋文的真實意涵。
人類學系的訓練課程的另一個特色是必須出田野。大部分都是在大三的時候修田野實習課程。田野課程讓學生開始接觸台灣島內的異文化,例如原住民文化,或漢人農村文化,或漢人漁村文化等。不像現在學生在高中,或大學,就已經可以參加社團活動接觸到台灣原住民文化。現在電視頻道有原住民電台,很多原住民也到平地工作求學或生活。原權會或其他原住民團體經常在媒體出現。當年原住民生活範圍相當集中在原居地,到平地的原住民不多,原住民意識不強,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隔閡相當深,如果不是專門研究員住民的學者專家,平地漢人幾乎不會接觸原住民。筆者大三田野到卑南族的南王村的確有文化衝擊,卑南族人招待我們吃檳榔,喝小米酒,我們還觀看猴祭,少年會所,女巫的治病儀式等,對我來說都相當”exotic”,符合典型「奇風異俗」的人類學研究題材。
大學部的課程多數是由老師講課,同學抄筆記。很少分組討論或學生上台報告,而是學生每人各做自己的筆記,期中考與期末考時分出勝負。有的老師連期中考都不考,只給期末考,「一考��定江山」決定及格或不及格。碩士班課程就由學生輪流做口頭報告,但是由於修課人數很少,也很少分組討論。例如筆者碩士班一年級入學五人,去掉考古學一人之後,剩下文化的四人,根本無從分組討論。課堂上要用的書,在學校內一定找得到。當時人類系自己有圖書館,在系館的地下室,老師上課用書或學生借書非常方便,幾乎不需要搶書或預先訂閱。如果要用文學院圖書則到文學院圖書館,位於文學院中庭後方。另外還有鄰近的總圖,以及法學院社會系圖書館,法圖(法學院圖書館),都是筆者常光顧的圖書館。當時尚未有中央圖書館。台大圖書館幾乎就是全台灣最齊全最專業的圖書館了。當年所有圖書均為紙本,沒有電子書或網頁資料可參考,寫報告一定要到圖書館找書。
當時教學輔具很簡陋,沒有投影機(放一張透明紙,上面列印圖片或文字),更沒有powerpoint。頂多只有幻燈機(可以放映一張一張的照片正片),以及原始的一張嘴講課。後來畢業以後逐漸有投影機,我在民族所學會製作投影片。一九八零年代有了電腦,大家忙著學習各種打字輸入法(倉頡、大易、注音)。原先學習抄寫製作的讀書摘要卡片(厚紙印製的),成堆成堆地現在都沒用途了。這些卡片有專門工廠印刷讓我們購買。
當時台灣尚無人類學博士班,碩士畢業之後筆者到中研院民族所工作,幸好國科會有補助出國研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由於在台大已經受到這樣的英文與田野訓練,出國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博士課程時,對於學校的要求都能勝任。不習慣的是,日常生活上消失了中文,完全要以英文來取代,以及周遭人際關係的轉變。學�校方面則沒問題,比起其他地區來的學生台大學生都能很快地進入軌道。赴美第一年結束即通過相當於碩士水準的口試測驗,順利進入博士班課程。回台作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迅速地前後五年之內取得博士學位。這都要歸功於台大人類學碩士班課程設計與碩士論文要求田野調查的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