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
陳建源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2013年以中文系新手身份出道的我,每當以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的身份在各種學術場合介紹自己,總是有許多人類學及中文領域的朋友表示「我聽過你 !」,久而久之,也十分習慣以「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來介紹自己,接著總會被追問開設何種課程,當回答到「大學國文」時,總是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且會自動忽略我接下來所要說的「文化人類學及田野調查等科目」。非常有趣的是,學界朋友們對於「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的直接聯想, 往往連結到文學人類學、或是禮記裡的儀式、詩經中的風俗等想像,然而作為觀光人類學者及流行文化研究者的我,只能暗道「我辜負了眾人期待」。
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在首度披掛上陣時的心理狀態大概只有「無照駕車」可堪形容,儘管這種不必擔心被取締的「無照駕車」心理狀態現在想來十分有趣。 回想駕駛上路的當時,焦躁卻未曾因此稍減,過度僵硬的身體使人容易投注過度的專注力在眼前的視域,而對路上出現的任何風景視而不見。被迫上路之後,一開始還得付出極大心力、搖搖晃晃地學習油門操控,等到因為交通規則與道路的不熟悉所造成的緊張感逐漸消失後,卻也慢慢可以享受這心理狀態,進而開始欣賞沿路景色。
站在兩者之中,重新思考書寫問題
以往「中文書寫」在台灣社會常被認為是最不需要練習的,理由可能有許多。 主要理由不外乎是我們透過國文教育從小練習到大,身經百戰的台灣考生們豈會連篇像樣的作文都不會寫,然而實際困境卻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嚴重,例如今年的國中會考作文題目〈捨不得〉裡,眾多十五、 六歲同學以爺爺奶奶過世的不捨出發,書寫至親過世的不捨,這些同學的共同症狀也被閱卷教授指為過度消費爺爺奶奶。此外,針對上述「共同症狀」的反省,也被作家朱宥勳歸咎於中文教育裡的「缺乏創意」,「生活經驗貧乏」的學生為了高分去書寫主題正確的作文。
連國中畢業生都已如此僵化,更何況是接受「中文教育」更久的大學新鮮人。 實際的書寫困境在於:同學們付出了太多時間在沒有意義的書寫,進而否定書寫原本作為溝通以及承載知識的功能,而這樣的輕視,又導致了書寫本身的弱化。讓我先以兩個親身體驗的例子來說明實際面對的書寫困境:首先,在一個聚會閒聊場合中,一位老師半開玩笑地提到「你們中文系可以教學生寫一下email嗎?我深夜收到的一封mail問我,明天下午三點約在某地見面,卻沒有說他是誰,也沒問我同不同意。」我則是以「做人失敗是大學中文系該負責的嗎?」笑笑回應,然而有過大學教書經驗的同仁都知道這絕非個案。另一個例子,是在批改課堂作文時,得容忍連串模組作文�與祝福慰勉法的糾纏,祝福慰勉法的展現在限時完成的課堂寫作就是連串驚嘆號,或是「人生豈不美好? !」等牛頭不對馬嘴、神來一筆的「問號加驚嘆號」的駭人收尾。為了對症下藥,我也曾在課堂上半開玩笑地說:「以後看到最後一句是以驚嘆號結尾的先扣五分,雙重驚嘆號則加倍扣分。」前述失禮的來函、制式內容及連串驚嘆號使用的狀況反映出一直以來的寫作教育問題,這不僅是不良寫作習慣的累積,也因為學生長期試圖滿足閱卷者的期待,而造成敷衍性質的模板作文不斷產生。思考表達的單調及缺乏寫作邏輯的書寫在生活中一再出現,也造成書寫脫離日常生活並成為單純的考試工具。
其中,我認為主要的書寫問題在於如何讓學生捨棄堆砌文字的壞習慣,而能 「反璞歸真地」具體陳述出所要表達的內容。這說來簡單,但在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因為中興大學的學生多為理工、生農背景,人文社會科院的學生佔相對少數,在如此的學生組成下,要如何引發學生共同興趣,讓學生不會想當然爾地寫作,在起初時常困擾著我。菜鳥教師如我,只好不斷透過教育部閱讀書寫計畫以及教學工作坊的參與心得來進行試驗。幾經挫折之後心念一轉,回想起自己接受的人類學訓練及民族誌撰寫的步驟,告訴自己不如先放下眼前的教學目標及文本,重新回到民族誌書寫之前的重要的準備工作,也就是回到觀察力的培養及紀錄並就觀察所得來分析及進行書寫。同時,要求同學透過日常生活觀察以找尋在地文化的蛛絲馬跡,並傳授紀錄方法,這對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來說輕而易舉,不但解決了起初無照駕車的焦躁狀態,同時也把自己從學生惱人的「八股書寫」中解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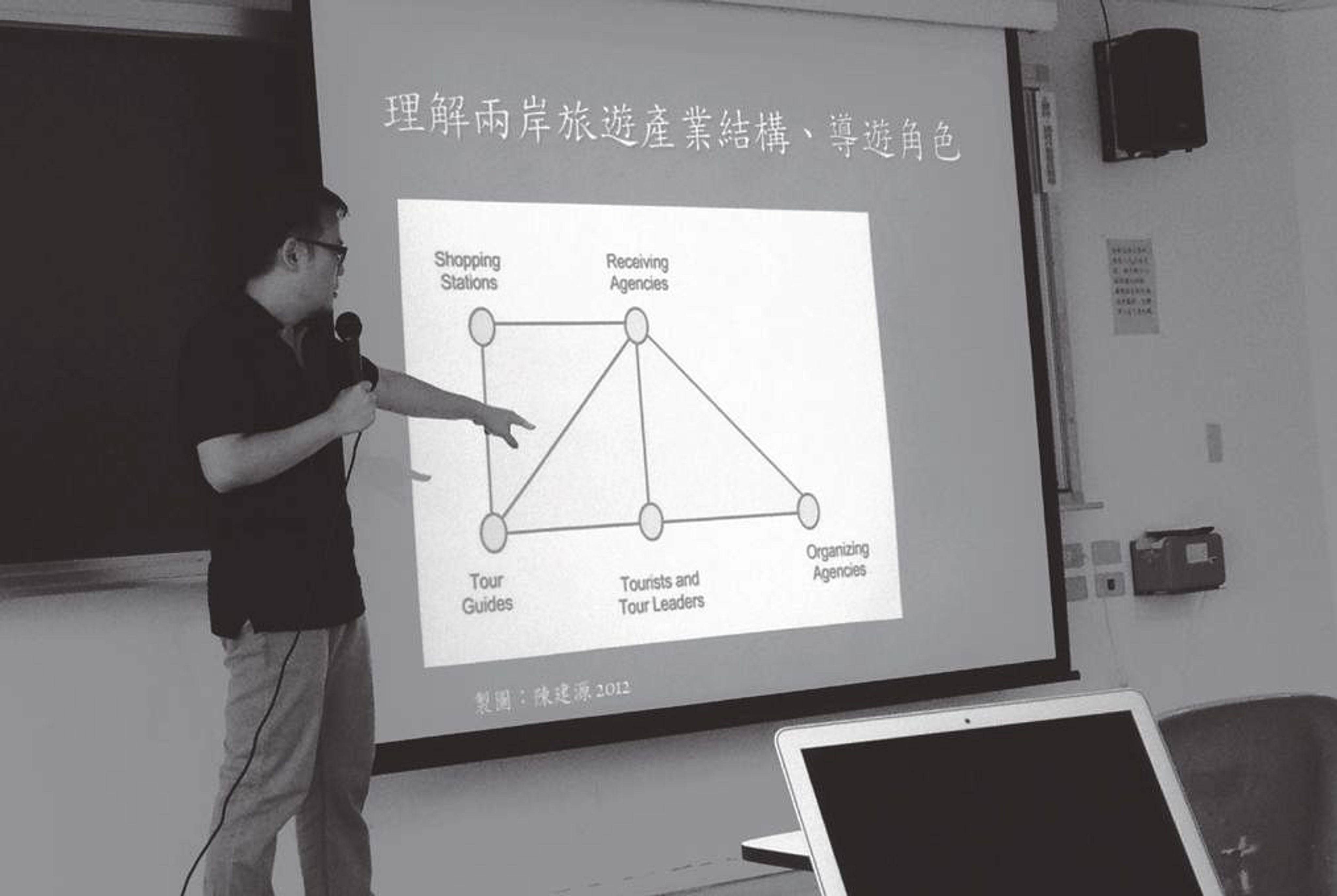
高雅寧 攝
之後,我就展開一連串讓同學以觀察為基礎的書寫練習。以其中一項課堂作業為例,「台中風景明信片」的設計鼓勵同學不只當個來去匆匆的台中過客,而是透過在台中大街小巷穿梭的過程,不斷地找尋「值得看的風景」,並將內心有所感悟的人文或自然風景以影像及文字記錄下來。重新在熟悉中找尋陌生,在陌生中重新發現經驗裡熟悉的風景,讓學生在透過觀察、紀錄以及書寫「文化」的過程,將手邊俯拾即是的台中在地風景及文化記錄下來。不標榜社會科學方法的田野調查以及不強調民族誌書寫的都市觀察紀錄,成為同學在大學國文課堂裡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作業。不期待同學在完成一個作業後, 就能立即回應台中出身的作家劉克襄所提出的「為何城市失去了光榮感?」的嚴肅問題,但此一作業讓許多台中在地同學, 透過探訪曾經熟悉的街景,找到都市快速變遷下的過往生活記憶,人類學方法中的 「觀察、紀錄與書寫」重要性可見一斑。
另外一個作業「一週餐桌紀錄」則採取類似簡易的自我民族誌形式,請同學記下完整一週的飲食內容,並在便當、泡麵、雞排等各式宵夜及手搖飲料中,運用 「反思」去觀察並分析自己的飲食與社會生活。以自我民族誌的形式引導同學去察覺作者自身在文本裡的角色,也就是以更細微的觀察去掌握敘述中的「我」,並將種種觀察方法導入,透過同學對個人飲食內容的解讀,引導個人去體會飲食背後更大的家庭、產業結構及社會生活的存在, 體會個人飲食生活從未非常「個人」。除了「偏食」與「快速」的日常飲食體會外,有同學省思了「獨食」背後透漏出的不與他人聯繫的孤獨狀態,也有同學提出了「雞排加手搖杯」在大學社交圈裡的重要份量,結合日常飲食觀察紀錄與飲食書寫的文本的閱讀,同學逐漸能體認到飲食生活中內蘊的文化層面,描繪出各式飲食所繫的文化認同、社會生活或親情等層面,並就「味覺」做出細膩描寫,而非陷入當下美食節目常以缺乏想像力的單調語彙描述食物味道的窘境。也因此作文不再是單純提筆作文章,而成為將日常生活所感知的細部文化轉化為具體文字並詳實記錄下來。
以上在「無照駕駛」狀態所設計出的作業,對中文系或人類學師生而言都不陌生,也都能在各處發現似曾相識的版本。在中文學界業已有許多努力把課本當文本 (民族誌)閱讀,再轉化當成寫作素材。將文化現象的轉譯當作是書寫的一種形式、甚至是書寫的目的本身,並將此一「觀察」方法介紹給修課同學,就成為我在大學國文課程中最重要的目標。懷抱此一目的,包括散文、 小說外的各種電影、短片、及廣告都成為理解文化的重要文本,用來協助課堂討論並用以深化同學的觀察分析能力。
站在學門之間,��推展學科白話文運動
這些在中文系裡的小小努力,也與我和一群志同道合好友共同展開的「學術白話文運動」有關。隨著與中文及人類學兩學門友人的交流日深,且因自身所處的特殊處境,常會聽到不同的學門陳述各自的危機,這兩個學科所面對的共同困境, 一是學科教育目標的確認,二是畢業生所面臨的就業市場萎縮問題。身處學界中的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將腳步停留在呼籲國家正視人文價值,但身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或許也能選擇積極面對人群並進行開拓市場的工作。
身處兩學門中間的我,剛好拉開了些許距離客觀地來看問題。在中文學界, 最近引發熱議的「台灣中文教育的未來走向」問題,除了對中文教育目標的質疑,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視為對於「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再商榷,既然提到了「文化」,身為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當然就找到了著力點。與許多在中文學界的同儕意見一致,我也贊成唯有掙脫道德傳授或公民教育,重新以批判及開放的態度理解華語文學,文學與文化才不會變成當代人的「身外之物」。在人類學界,除了學科常被稱作「人類文化學」或是印地安納瓊斯的學科這樣的微小問題外,人類學還需要面對比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更形嚴重的就業市場萎縮問題。與此相對,人類學的參與觀察、田野調查甚至是「說故事」方法卻成為目前流行的業界方法。文學、商業、設計及旅遊業界開始注意到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說故事及創新,並期待用在新產品的推出上,然而其間人類學者的參與卻是屈指可數。實際經驗也說明了這個演變方向,在幾場我參與組織及協助主持的人類學/社會科學的白話文 (學術科��普化 )講座中,大約會有一定比例的聽眾對於田野調查方法及運用展現出高度興趣, 在Q&A時也會持續追問將方法運用在其他相關領域的可能性。前述觀察顯示了並非人類學或其方法不受歡迎,而是現今人類學的關注議題能否足夠「入世」以協助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樣議題。唯有同時關注學科內的理論發展趨勢以及學科外的社會議題,並努力做出回應,對於接下來的學科「入世」議題才不會只能被動地回應。
以上就是我無照駕車的小小心得。

高雅寧 攝
備註:
1. 邱瓊平,〈作文「捨不得」一堆爺奶過世 教授質疑虛構〉,《聯合晚報》。
2. 朱宥勳,〈為什麼作文裡都是阿公阿嬤?〉,��《udn鳴人堂》
3. 劉克襄,〈從台南觀看台中〉,《自由評論網:自由共和國》。
4. 我曾協助過「百工裡的人類學家」相關的演講活動擔任主持及與談人的工作,目前也同時擔任A舍 (A-sia Studio)的共同召集人,負責亞洲研究的「科普化」推廣工作,所以觀察樣本都來自這兩個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5. 有關學科的「入世」問題,鄰國日本的「強迫入世」走向及所造成的學門存續危機,值得我們思考。日本文部省在今年六月提出國立大學將逐漸走向「廢除及調整教育系及人文社會科學系所,並協助轉向社會所需要的領域」的方針,雖引起日本教育界的強烈抗議,但是日本的大學改革方向,尤其是針對高齡化、少子化威脅的台灣而言,絕對是種重要的提醒。日本經濟新聞,〈教員養成系など学部廃止を要請文科相、国立大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