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敏感度的醫學教育實踐
顏芳姿 | 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你不是醫生?不是,我學人類學,來醫學院臥底 !
2007年從澳洲念書回來,別人常問我:為什麼在醫學院教書、教什麼?當時適逢醫界大老推動醫學教育改革,這個浪潮將我帶進醫學院,在通識教育中心教醫學人文。醫學人文是什麼?簡單地講,就是陪伴醫學生擴大關懷,從不同的角度找尋真相,從而對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包容。
人類學可以研究人類社會無限多的領域,醫療人類學這個學門自始即強調病人不只是生理的存在,更是一個社會性、 文化性的深層存在。圍繞在病人身上,有很多生活、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影響他們的健康,想要讓他們恢復健康,必須尊重他們對身體、自我、性別、社會關係和健康相關的文化觀念。因此,有時候政治經濟的變革、性別關係的轉型、文化觀念的溝通比醫療介入更有效。哎 !把這種人類學家放在醫學院,無疑是與放諸四海皆準的醫學唱反調。那為什麼還堅守崗位呢?因為醫療人類學家可以培養很不一樣的醫生啊 !全球化的時代�,能服務多元文化族群的人才,往往在經濟不景氣,企業裁員滾滾的情況下活存,還能勝出。日本全球教育與訓練顧問公司執行董事布留川勝說,他擔心,日本上班族可能在5年之後面臨嚴重職業危機。「確實該好好想想,自己如何全球化。」醫學院裡面的人類學家恰恰是培養醫學生全球化的能力, 讓這些醫生勝出。
在國外,人類學家早已攻佔醫學院、 公衛學院和護理學院相關的必選課程。其中,醫療人類學教的是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指的是與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人能有效的溝通互動、解決問題,目前在醫療照顧上受到高度的重視。醫生具備這種能力,能夠服務文化或價值觀不同、社會階層、甚至是不同國籍的移民, 具有文化敏感度 (cultural sensitivity ),不僅能適當地與多元文化族群互動、溝通,還能提供文化適切的醫療照顧。2009年起, 我每年都開「新移民與多元文化健康」課程,其中一個行動學習是與新移民「共學」。這個課與板橋社大新移民識字班合作,第一次先跟新移民認識,參與社區大學的中文課程,志工老師與新移民討論的內容是家鄉小偏方,學生在旁邊做參與觀察;第二次是醫學生與新移民透過戲劇演出,交叉提問。這種教育方法受到Paul Freire的影響,盼望「對話」、「交叉提問」鬆動現行的新移民健康政策和醫療行為。為什麼要進行交叉提問?
1、新移民面對的對象是醫學院學生,他們將進入醫療專業和提供醫療服務,但目前不具權威地位,有利於姐妹提出自己的看法。學生年紀比新移民小,學習傾聽新移民觀點。在還未形成明顯權力關係的情況下,雙方平等的互動。
2、學生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好奇新移民就醫遭遇到問題,能引起他們主動向新移民學習。
3、過去制定新移民相關政策,從來不問新移民的意見;新移民對於歧視性的政策或者移民人權往往需要透過抗爭的方式向政府爭取。這次共學提供另一個形式,讓從未參與決策的新移民與未來的醫護工作者一起從共學的行動中反省就醫問題。新移民向學生發問的過程,覺察自己的處境、矛盾衝突等問題以及提出自己的看法。兩者共學,在辨證中邁向問題的解決,並共同推動醫療環境、醫療照顧品質的改善。
這些行動學習讓學生深入了解文化的影響力,如新移民女性看婦科時對醫護人員特定性別的期待,反思台灣婦產科為何形成以男性為主的天下?新移民和台灣人做體檢各發生在什麼不同的狀況?新移民醫療自主權如何改善?
至於如何改變,由醫學生透過劇場的方式與新移民 (醫療服務的對象)互相提問,共同探究、釋疑、深入了解新移民的生活世界和看法。劇場的活動包括醫學生演出新移民就醫七分鐘的小戲,創造醫學生與新移民互相進入提問的媒介,接著由演完戲的同學圍坐在新移民身邊,聽聽觀眾的看法。一方面,戲劇裡面根據質性研究發展出劇本,每一幕都有真實的人、真實的實例,演出新移民碰到的就醫問題。 另一方面,透過兩者沒有距離的互動,互相提問,未來的醫護工作者能深刻地體認到新移民的問題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課程一開課,學生就知道有這項演出。��這個集體的創作成為學習的動力,讓他們有步驟地接觸新移民在陌生環境語言的不適不便、認同的多樣性、新移民遭遇到的歧視、監控和污名,了解新移民做了哪些反污名的行動、如何爭取他們的權利,並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繼續改善有關新移民健康的相關人權和醫療問題,產生真實的反省和行動。在蒐集個案、發展劇本和編劇排戲的過程中,一次一次親身了解新移民就醫問題的爆發點在哪裡,並形成戲劇張力,做一個演出,呼喚新移民切身或者身邊朋友的經驗,由新移民給與醫學生迴響,互相繼續討論。
其次,文化敏感度有助於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引導醫生能尊重病人的價值、偏好、表達的需求,除了病人感到舒服之外,情感的支持,並消除恐懼、焦慮。這不僅對醫病溝通有幫助,更重要的是醫學生學習面對疾病、也面對病人,醫生和病人可以進一步共同協商治療計畫,有醫生可以做的部份、也有病人可以做的。更重要的是,醫學生學習醫生如何進入病人的世界,從病人的眼中了解疾病。
國外的醫療人類學家時常觀察醫學教育、臨床醫病互動和醫學倫理,在機構內可以協調、整合照護,從觀點的提供、醫病溝通和倫理的考量等,檢討醫療有問題的個案。醫療機構對病人來說,雖然是人生的過渡,但也能給與持續而不是一時的幫助。醫療人類學的課程結合這些跨領域的合作實例,可以幫助醫學生學習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顧,可以改善醫療體系,提高醫療品質。
踏入醫學院,我很感謝長庚醫學系。 當時,為了開97年下學期「醫療人類學」 的課,我規劃「醫院中�的田野」。柯毓賢醫師問我,在醫院哪個地方可以遇見文化?我當時找了中醫部,讓學生在這裡做 「病人訪談」 (patient interview),傾聽病人的心聲能提供醫學生了解經驗、行為、 感受、意見、價值、意義和文化知識。學生在這裡探討為什麼台灣的癌症病人看西醫、也看中醫?目的有二:一從醫療選擇理解台灣漢人如何進出西醫和中醫的醫療照顧體系;二是 (西醫)醫生從「跨文化醫療照顧」 (cross-cultural healthcare )的角度, 能擴大理解並支持病人在西醫治療期間有使用中醫調理的需求。進行醫院中的田野,學生學習如何引發病人談論對疾病的解釋,經歷過治療之後的身體經驗和治療選擇。初次訪問癌症病人令學生充滿不確定性、恐懼、不安,我在他們正式接觸前,進行訪談練習、倫理問題討論和從旁輔導。不過,這次親身接觸病人的經驗讓學生貼近病患、接近服務對象,有學生提到「比任何教科書都更令人成長、令人感同身受」。學生原本所準備的訪談問題,遇到受訪者,訪談內容就有了變化,他們因此長出臨場應變能力,保持對受訪者的興趣,繼續主導訪談,讓學生深刻地了解到病人觀點與他們所預設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更有學生說:訪談顛覆了以往的認知,察覺到一直以來刻意忽略的東西,從病人的訪談產生對生命的感悟。

顏芳姿 提供
這個規劃後來發展為我在國防醫學院教「病人醫師與社會」這個課程,前半部討論醫療人類學議題,接著是敘事醫學單元。這門課我會問學生:當你選擇當醫生,一輩子的工作都跟病人密不可分,問題是怎樣照顧病人?醫生沒有經歷病痛, 不可能了解病人的感受,將心比心很難一步到位,正是因為很難,我用整學期陪伴他們學習。敘事醫學單元詳細討論病人訪談倫理守則和程序,進行訪談練習,課堂討論不同類型的醫師,讓他們扮演,親自照照鏡子看看執業醫師的臉色和口氣,病人會有什麼反應。每次我會邀請一位素昧平生的癌症人到課堂上分享抗癌經驗,由我做病人訪談的示範教學,學生進行觀察和提問。接著設計路線讓學生以病人的角度全方位觀察醫院動線、門診和病房,之後,親自訪問病人,寫一篇自己的病人故事,將人生第一個病人牢記在心,提醒自己理解病人的感受,從病人和家屬的立場考慮治療計畫。遇到執業生涯的難題,能運用這次敘事醫學的經驗,整理自己面對病人生死的衝擊、困境和情緒,重新再出發。經過敘事醫學這個單元的學習,他們學到在工作中融洽的與人對談,從中獲得對方的看法,問出醫者想要獲得的東西。 避免因為忙,或者怕醫療糾紛,醫護人員用標準程序SOP處理,忘了站在病人的立場考量。
醫學院的人類學課程強調理解、尊重、包容各種「差異」,從出生到死亡, 很多文化與西醫主導的身體和健康觀念都不同。醫療人類學家試圖打破理性、客觀、冷靜的醫學知識,希望學生能重新定�義醫學,做個另類的醫生。如果能增加醫學生對人的好奇、觀察、理解不同階層、 社會背景的生活世界,以及尊重和適當的回應,相信學生更能縮短文化、階層與性別等差異的距離,成為跨文化醫療的橋樑。我們相信彼此融入、相互了解,能夠產生本質的改變,這個改變先由醫學教育開始,接著會在醫護工作者和健康政策等等地方遍地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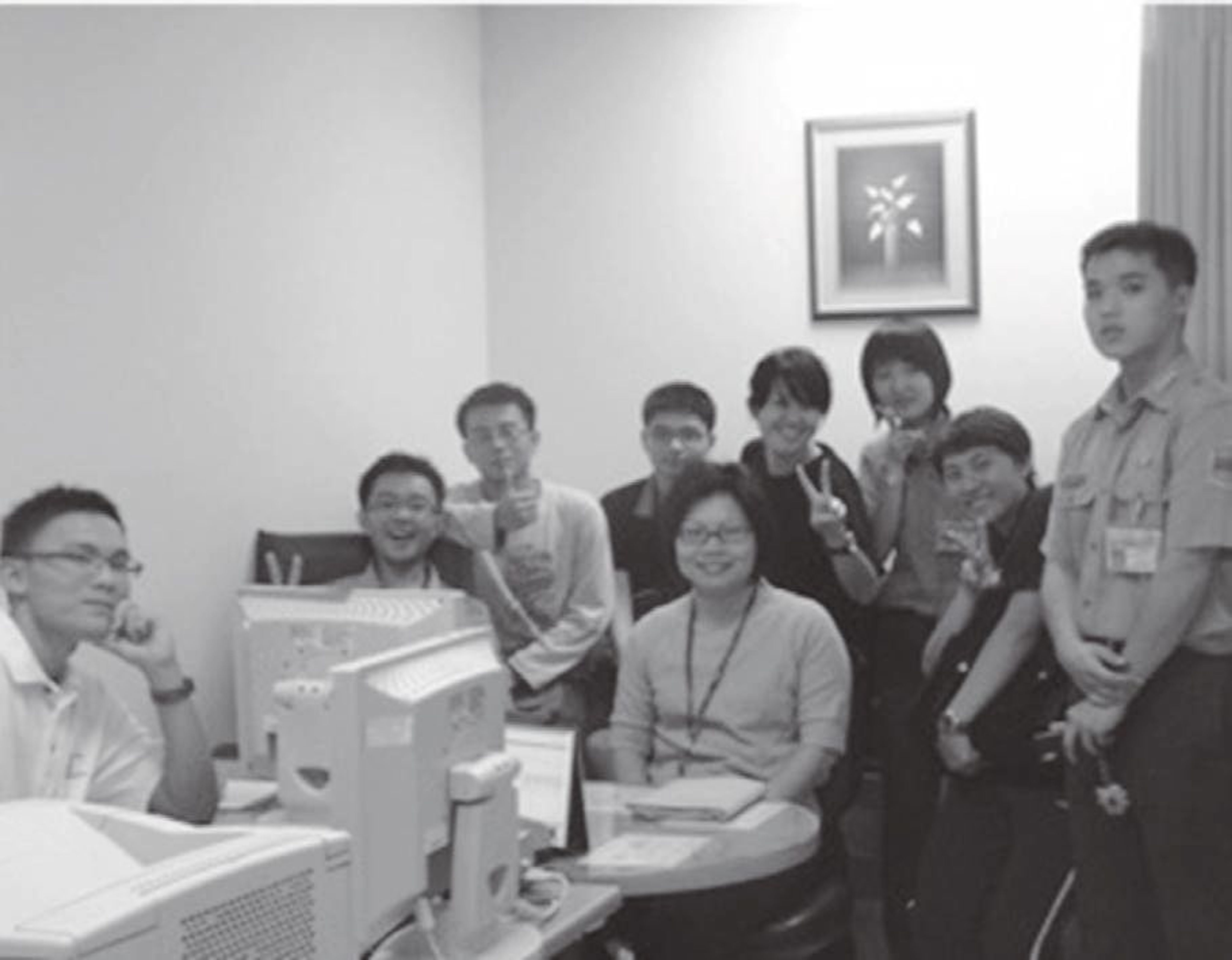
顏芳姿 提供

顏芳姿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