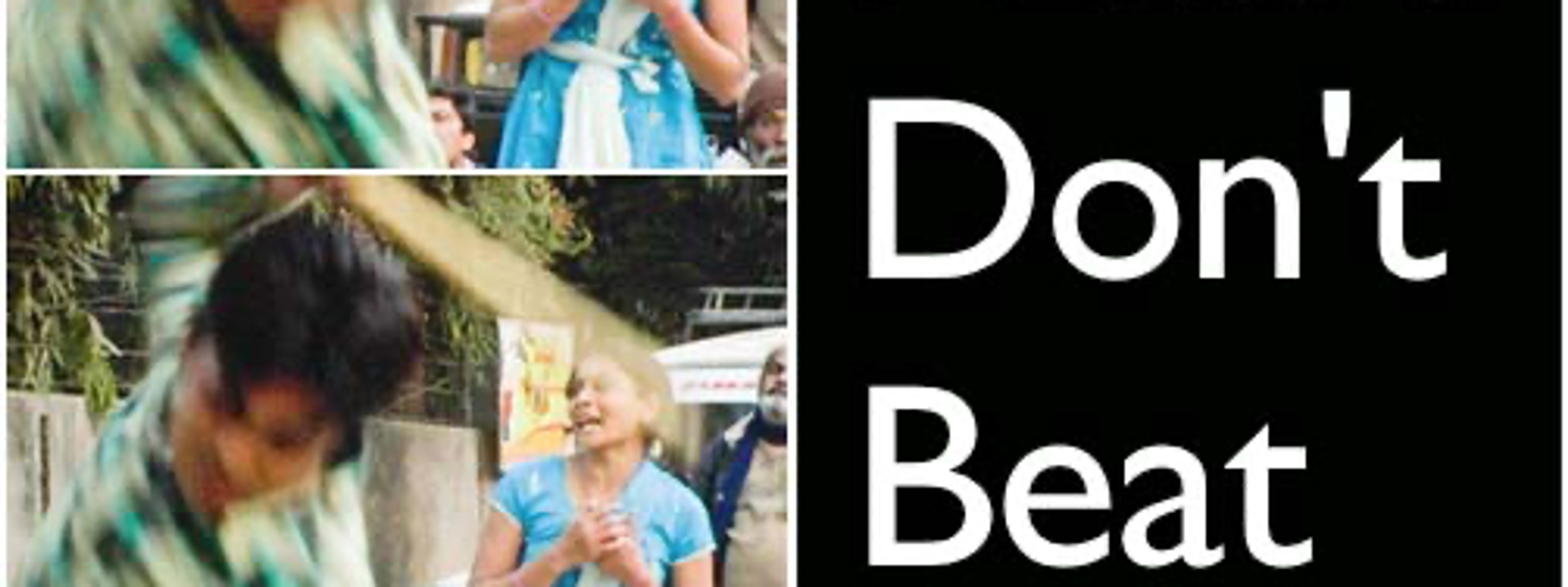Please Don't Beat Me, Sir!
專訪傅可恩 (P. Kerim Friedman) 教授
人類學視界編輯部 採訪
前言
人類學家會看電影,那人類學家會不會拍電影呢?他們會拍怎麼樣的電影?中間又會遇到甚麼樣的困難呢?這一期的人類學視界我們很榮幸能夠訪問到任教於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的傅可恩教授。他的專長是視覺人類學和語言人類學。研究主題是臺灣的語言與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的關係。除了論文書寫以外,傅可恩教授和他的電影工作者太太夏雪莉女士(Shashwati Talukdar)長期拍攝和印度的「犯罪部落」─「查拉」(Chhara)相關的議題。這次他們帶來製作長達五年的新片Please Don’t Beat Me, Sir![1],這部影片目前已經得到美國影像人類學學會(Society for Visual Anthropology)的最高獎項「尚��胡許獎」(Jean Rouch Award for Collaborative Filmmaking)[2]。並入選2011年的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以及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印度目前有198個「犯罪部落」(Criminal Tribes),Please Don’t Beat Me, Sir!便是討論其中一個部落─「查拉」(Chhara)的故事。這個部落和其他犯罪部落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有一個劇團在為他們發聲─「布德漢劇團」(Budhan Theatre)。在英國殖民印度時期,為了治理方便,英國官方開始有一系列的「警察民族誌」調查少數民族,並在1871年通過「犯罪部落法案」將查拉在內的遊牧民族標記為「犯罪部落」,並且認定他們天生就是罪犯。就算到了印度獨立之後,這樣的狀態仍然沒有太大的轉變。在1952年時,尼赫魯政府將原先的「犯罪部落」更名為「除名部落」(Denotified Tribes),但是警察與其他人民對待他們的方式仍和以前沒有太大的不同。而「布德漢劇團」就是為了要改變這樣的狀況而成立。他們的首部劇作,同樣也是他們團名的來源:《布德漢》,便是以藝術的手法呈現一位被警察刑求致死的Saber人布德漢的故事[3]。
Q:怎麼開始拍「�除名部落」(denotified tribes;以下縮寫:DNT)?前製作業大概做了哪些準備?
A:我太太一開始拍了一部關於作家和社會運動者,也是除名部落社會(DNT)運動發起者MahaswetaDevi的紀錄片,在拍這部片的過程中,她去了印度第一個除名部落會議,在那裡她觀賞並拍攝了布達漢劇團的表演(她也有把這個片段放在她的電影中)。之後,在2003年我們聽到Dakxin[4]被逮捕的消息,我們非常擔心。雖然他被釋放出獄,他的案件在當時仍然懸而未決,因此我們在2005年時飛到印度拍了一部關於他的短片。這部影片就是Acting like a Thief[5],我們在幾個禮拜內拍完,並且放到Youtube上面。在拍這部影片的時候,我們喜歡上這個社群,在加上布達漢劇團的戲劇作品和社區發展工作的品質與細緻程度都讓我們印象深刻。因此我們決定拍一部紀錄長片。我們用Acting Like a Thief這部片在網路上募款,並開始拍攝Please Don’t Beat Me, Sir!。
Q:那你跟你太太拍片的時候是怎麼合作?
A:最普通的樣子是,我攝影、她做訪問,然後有另外一個人幫助我們錄音、或者是我太太她會錄音,現在還是這樣子。
Q:她主要是做剪接嗎?
A:她是做剪接家、因為她很會剪接。她之前在Michael Moore的電視節目,做副剪接家的工作。所以我們大概拍電影的方式,大部分是先剪接每一個小鏡頭、先把所有訪問剪接好,我們會一起看,然後討論順序,再剪接,再看、再討論。因為這部電影是合作,所以更複雜��,我們會把電影帶回去給他們看、跟他們討論,自己再討論一下、再去拍一些鏡頭回家,再繼續做,這個過程很長,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在做。
Q:那這種跟當地人合作的方式,是一定要支持他們的立場還是你們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A:可以這樣說,我們是跟布達漢劇團合作,不是跟整個部落合作,因為部落裡面有衝突,但因為他們是運動者,他們有一些目的,我們支持他們的運動,但不一定支持他們所有的想法。比方說,你可以看他們自己拍的紀錄片,他們大部分都是在說「除名部落」的少數民族都是受害者,他們不要討論自己部落內部的一些衝突,可是我們覺得為了一個紀錄片一定要討論那些衝突。所以我們的電影就有討論一些他們不想討論的一些衝突。我們這樣做還是有受到他們的同意,所以,我們這樣做很難說是不是他們的立場。如果你給他們一個攝影機、請他們拍,他們不會這樣拍,因為他們比較會避免那些問題,但我們拍了之後,他們覺得我們這樣拍才對。
另外他們要我們避免討論偷東西的方式,這個我們電影裡面沒有討論,這個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因為在訪問裡,他們有說小偷也是一種表演,所以我們要討論,可是我們怎麼可以討論,如果沒有辦法討論他們怎麼做?我們在電影裡面也有他們開會的時候在討論這個問題。可是後來他們看了草稿之後,他們自己覺得、我們電影裡面缺他們父母那代的故事,所以他們後來說:「如果你討論的是他們那代的要求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你可以討論我們父母是小偷這件事情。」所以你就看我們裡面有在討論,有一個鏡頭是演員跟他爸爸,他問他爸說:「你為什麼不要我跟你走這條路?」因為他爸爸的地位很高,部落裡面很多人聽他爸爸的聲音,當他爸爸願意被訪問之後,很多人也願意被我們訪問了。最後我們還是達到目的,我們還是討論過我們需要討論的事情,雖然我們沒有很仔細的討論那些過程,可是其實那些過程沒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他爸爸在說:我做的工作也是一種表演,那這樣就夠了。
當然我跟你講,有一個法國的導演他的名字是Bresson[6]。我們本想要用他在Pickpocket中拍小偷的那些鏡頭。因為我們覺得那些人很會做,如果可以給人家看他們怎麼做,別人會覺得他們很優秀,不會覺得不好。可是他們覺得這樣做不太舒服,所以到最後我們就放棄了,只放那個會議[7]。我們還是覺得這樣做比較有趣,你又可以看到部落裡面的一些衝突,因為部落裡面開會講了多很有趣的話,像是他們會說:「一些小偷一直給我們很多的幫助,我們不應該害他們。」
Q:剛談到跟當地人合作的情形,不曉得你們影片最後在討論性別時,是因為女性的地位在當地的電影也不常被討論嗎?
A:我們討論性別有三個原因,因為劇團他們有圖書館也有另類學校、也有一些年輕人參與那個劇團,所以裡面我們拍了一些女孩子。有一天,劇團突然告訴我們:「他們很擔心,那些女生會離開、因為她們要結婚」是他們告訴我們這件事,所以我們才開始拍這個題目。後來劇團自己演了Mahasweta Devi寫的一個女性主義戲劇,就是我們影片最後面記錄到的表演。第三��個是,劇團裡面有一個很優秀的演員Kalpana,她自己的生活情況也是碰到一些壓力。就是因為這三個原因,我們就覺得性別跟這個劇團是有關係的。
劇團支持我們這樣做,我們除了拍紀錄片,後來自己也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Vimukta[8],為了幫助那個劇團在美國募款,因為他們在印度有辦法募款,可是在美國沒辦法募款,目前我們給他們的錢都是為了圖書館,我們有討論如果這個電影成功的話,很多人會看電影,希望能讓很多人會支持他們的行動,所以現在跟他們討論,如果這個成功的話,我們能不能募款做一個給女生的獎學金,而這個獎學金唯一的要求:如果家庭要拿那筆錢,就要保證那個女生至少到大一或是到大四不會結婚。所以我們討論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可以顧慮到一些家庭,給女生一些機會接收高等教育。其實這筆錢不算很多,因為那邊學校、讀書費、課本制服不會很貴,所以我們現在在討論怎麼做。

Q:你們現在給予他們資源的一個方式就是在美國用基金會、透過這種捐款方式去幫助當地。那影片裡面看到,劇團的人可以獲得一些資源、建立圖書館並教育部落的小孩,那因此受益的人在部落裡面來講大概有多少?
A:其實這個很難講,那邊生活情況非常不穩定,你問很多學生教育的情況,他們會說:「我是讀大一、我是讀大二」,這個意思是他們可能讀到大一的時候,家裡就沒有錢繼續上課,或是成績不夠沒有拿到獎學金可能就要離開。劇團也是這樣,他們可能只參與一段時間。電影裡面有兩個小孩子,演出過短劇《我們的圖書館》。我們今年暑假回去訪問他們。其中一個孩子叫Harry,比較胖,還有一個比較瘦,比較瘦的已經在讀大學社會學。Harry那個時候是一個很好的學生,可是爸爸去世,其他家族的人給他很多壓力做家裡的工作,如果不做家裡的工作就會被家族的人打、可是做這樣的工作他會被警察打,所以他的生活就是要選家裡的人打他還是要警察打他。你看他這麼可愛、這麼優秀的小孩子,很快樂、也很聰明,現在連劇團也沒有辦法幫他。可是另外一個人因為受過圖書館、戲劇團體的支持,正在讀社會科學。所以就像你看這兩個孩子的情況,劇團當然沒有辦法幫助所有人。我也覺得離開戲劇團體的人,我看到他們的個性,我覺得跟其他部落的人也不一樣,你看他可能比較有自信,連Harry回來長大之後,可能會參與一些部落的活動、社會運動,可能會有這樣的影響,你沒有辦法知道影響在哪裡,所以這個就是很難說,也沒有甚麼統計。戲劇團體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要組織化。現在劇團得到一些經費,他們開了一間學校,會訓練其他部落的人,其他族群的人怎麼做戲劇,怎麼做媒體的工作。這個他們也可以拿到一個Indira Gandhi的 open university的證明,人去參與布達漢的學校可以拿到一個證明,證明他們修過這個課程。這個也會給他們更多自信,跟機會也可以賺一筆錢。
Q:所以你們會覺得應該要適當的介入當地社會還是你們會比較傾向拍direct cinema還是要拍一個有社會運動傾向的紀錄片?
A:我自己不會覺得某一種電影的方式是對、某一種電影的方式不對,我自己覺得是要看情況。那這種部落是一個非常弱勢的族群。他們受到社會歧視,很容易被剝削。我們拍這種電影的話,我們有一種自覺就是要跟他們合作。像Michael Moore拍的第一部電影就是Roger and Me是討論一個國際公司的老闆,像他沒有任何責任跟這種人合作,所以這種人已經有全世界的權力,所以像你用那種方式要看情況。

Q:片中有許多虛構的短劇部分,為什麼會想要用紀實與虛構穿插的方式?
A:有許多主題沒辦法用一般的紀錄片方式表達,例如:歧視、暴力和賄賂…等等。有的議題則是太過抽象而不容易拍攝(例如一開始的「Chharangar在哪裡」的短劇)。我們請求布達漢劇團的成員一人選一個主題然後寫一齣短劇。我們接著和他們一起合作把這些短劇改編成電影。
Q:拍這部電影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A:比較困難的地方..恩...阿....我想比較容易是講那個地方比較順利!每一件事情都很困難!你知道在印度辦事情什麼事情都很困難,不像在台灣什麼事情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那邊一個NGO給我們很多的幫助,叫做Bhasha[9]。如果不是他們給我們幫助,可能就沒辦法了。我們不只是跟布達漢合作,也跟Bhasha合作。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小小攝影師》(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拿到了奧斯卡獎。那個電影出現後,有一些印度的左派批評這部電影,為什麼?因為你看電影時候你會誤解:你會覺得拍電影的導演是自己去找這些妓女和妓女的小孩子,他去那些地方,好像是自己一個人去,他去那邊的原因其實是那邊的妓女已經組織化,已經有一個像是妓女的工會,但看電影你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可是我們拍電影,我們就是討論布達漢這個劇團,其實電影沒有看到我們,我們強調他們自己已經組織化,這個運動是他們自己的運動,不是我們的運動。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拍這個紀錄片有點敏感,就是要讓人看得到:不是我們導演去那邊拍,我們那麼優秀!其實我不會批評他們[10],因為他們如果沒有這樣做,他們沒有辦法拿到奧斯卡獎。一般你看美國關於印度的故事,還是關於非洲的故事,一定會有一個白人在鏡頭前面做翻譯,因為Hollywood還是覺得所有的觀看者都是白人,而且他們會覺得白人看其他的族群會覺得奇怪,所以需要一個白人做翻譯。因此我們自己很注意這個問題,就是不要用旁白,不要用專家幫他們說話。還是有我們的聲音,但是比較是在背後。可是我們還是覺得,他們自己很優秀,很會說話。特別是Dakxin和Roxy,這兩個角色,因為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人。所以我們覺得不要替他們說話。
Q:之前聽說導演想透過資料庫的方式回饋當地,那這個計畫目前進展如何?
A:我們在討論,因為這個很敏感。首先我們要確定資料庫裡面的資料不會傷害任何人。因為有一些人他們到現在還有法律上的問題。我不知道官方的人會不會看。如果所有的資料都在資料庫,那就很複雜,因為有兩百個小時,當地的人也沒辦法全部看。我們可能第一個是先做一些部分。就是我們可以拿到一筆錢,我們希望最後的光碟,會有一些口述歷史,有一些歌手,有一些戲劇的表演,可以放在光碟裡面先給他們用。可是其他的部分,我們還在研究。
註解:
1 官方網站: http://dontbeatmesir.com
2 Jean Rouch為法國著名電影導演與人類學家。他和Edgar Morin合作的《夏日紀事》(Chronique d’un été)開創了「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電影傳統。除此之外他在非洲和當地人合作的一系列紀錄片至今仍是紀錄片與民族誌電影的經典。
3 本劇的英文劇本請參見:http://indiatogether.org/bhasha/bhanplay.htm;中文翻譯請參見:http://zonble.net/archives/2005_12/824.php。
4 Dakxin是布達漢劇團的負責人,並且是《布達漢》一劇的編劇。
5 這部影片和夏雪莉拍的影片都可以在Der.org購得。
6 Robert Bresson,法國導演,著名作品有Pickpocket。
7 片中有一段劇團開會討論是否要拍攝偷竊過程的片段。
8 該組織網站:http://vimukta.org/
9 Bhasha是一個在印度從事原住民運動的NGO。
10 指《小小攝影師》的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