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婆、嬤嬤、娘娘與我
高雅寧|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廣西安德神農廟。(高雅寧攝)

廣西安德大村的村廟。(高雅寧攝)
「我們在廣西參加儀式時得知女性儀式專家在壯族農村中很活躍,我們沒有機會進一步接觸,妳有沒有興趣去看看?」一位學長如此建議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踏上了廣西西南邊境靖�西縣之旅,沒想到從此以後,參加壯族女性儀式專家末婆(mehmoed)的儀式,成了我田野工作的主旋律。1998年的一個冬夜,我跟末婆有了第一次接觸。當時我隨著廣西靖西縣未婆研究的前輩淩樹東先生與他的嫂嫂鐘秀英女士,到鐘女士娘家的村落裡,參與未婆媽倍所舉行的儀式。
基本上我就像「鴨子聽雷」一般,聽了一個晚上,那時我一句壯話也聽不懂,更不要說是速度超級快的儀式吟唱。我只能坐在邊上的板凳,盯著五顏六色的剪紙,看著儀式主家們忙進忙出,除了拍照與寫筆記外,剩下的就是感受儀式的氣氛。因為新奇,雖然是寒冷冬夜裡通宵的儀式,卻不覺得難熬。清晨時,我被安排在狹小的房屋裡,在半夢半醒中與鐘女士、媽倍同床休息了幾個小時。這就是我跟靖西末婆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1999年農曆過年後,攀親帶故一番,我住進末婆媽倍在貴水村的家。鐘秀英女士為媽倍遠房的姑姑,貴水村所屬之行政村的支部書記又是鐘女士的中學同學,因這雙重關係,在鐘秀英女士的引介下,我順利地搬進了媽倍家。雖然我清楚地表明我是台灣清華大學的研究生來此進行考察,但對當地壯人來說,只有末婆的徒弟才會住到未婆家個把個月,「研究生」根本不在當地的人的身分分類系統裡。因此當時有一個傳言,說我是臺灣來的仙女,要來跟媽倍學法術。儘管我沒有真正學了什麼法術,但是我確實就像徒弟一般,跟隨著媽倍到處去看她做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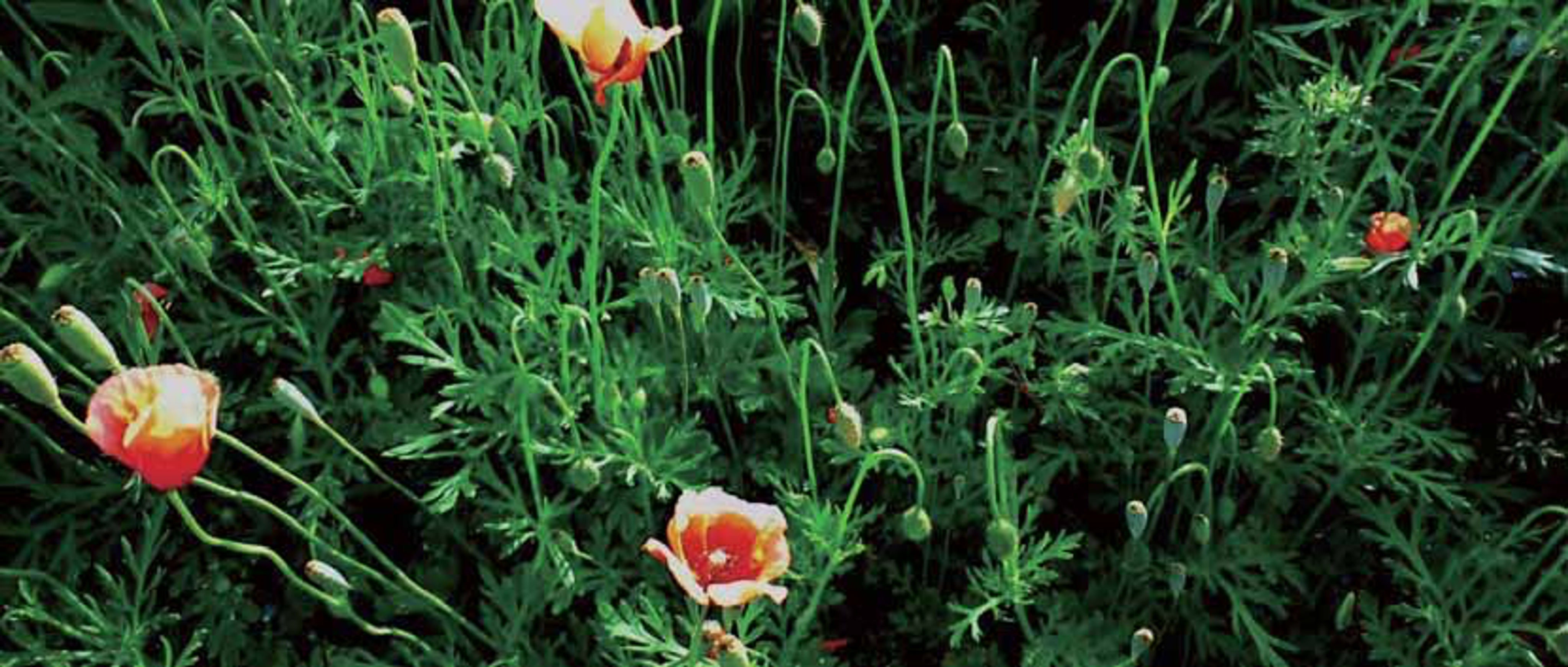
R‧かな提供。
2005年,我結識了靖西安德鎮著名的末婆仙娥姨,在我們還沒見面前,她就已仔細打聽我的「底細」。當時我透過安德鎮安德街民委員會支部書記的介紹,到大村拜訪幾位末婆,懇請其中一位讓我住到她家,並參與她所舉行的儀式。書記首先帶我到仙娥姨家,但她出外做儀式,大門深鎖。當天,我只見到海芬婆,她接受我住進她家,並隨著她到處去記錄儀式。不過,我最有興趣的「紀念民族英雄儂智高活動節」的儀式,那時是由仙娥姨負責進行的。儀式舉行前兩天,我小心翼翼地到仙娥姨家拜訪,希望得到她的首肯讓我參加與拍攝儀式。我前腳一踏進門,她便笑臉迎來,並為上次我來訪她不在家的事向我道歉。還輪不到我自我介紹,她就已經知道我之前在貴水村做過研究。於是我順水推舟,並鼓起勇氣跟她說我想拍攝她過兩天要舉行的儀式,她很爽快地答應了。仙娥姨主持的兩場儀式,後來就成了我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而仙娥姨也成了失戀時的「諮商師」。
田野工作中,除了住在末婆家與跟隨末婆到處去看儀式外,最常與我為伴的是一群在儀式中被稱為嬤嬤、娘娘的中老年婦女,她們中不乏「專業的」儀式解釋者與翻譯者。跟嬤嬤、娘娘的相處,讓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末婆儀式:未婆儀式之所以吸引人,還有末婆儀式雖然經歷過幾場政治運動而未中斷,��這絕對不是末婆自己唱獨角戲所致,而是需要這群嬤嬤、娘娘的配合與支持,她們是末婆的忠實「粉絲」。
在拍攝完仙娥姨主持的「紀念民族英雄儂智高活動節」的儀式後,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尋找能夠聽得懂末婆唱詞的婦女。仙娥姨是遠近馳名的末婆,門前的求助者絡繹不絕,根本沒有時間跟我坐下來一起翻譯唱詞。於是,我邀請末婆仙娥姨與當天參與儀式的部分婦女,一起來看我拍攝的儀式過程錄影帶。2005年4月的某個晚上,一群婦女們就擠在安德中學一位女老師的單人宿舍裡看「錄像」,大家都很興奮的看到自己在螢幕上出現,七嘴八舌的討論著。當時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看看到底哪位婦女比較熟悉儀式唱詞,經過一番觀察與詢問之後,有兩位可以翻譯的備選人出現了:一位是惠敏婆,一位是鄧姆。我當場詢問了仙娥姨是否願意讓我與這兩位婦女進行她的儀式翻譯工作,得到她的首肯後,在儀式的組織者一農小英女士的張羅之下,翻譯的工作正式展開。將近七個小時的儀式錄音,兩位婦女有空的晚上,在她們家事忙完後、睡覺前的兩、三個小時,捉緊時間翻譯,每一個晚上也只能翻譯與記錄約五分鐘的錄音,就這樣持續工作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完成任務。
翻譯工作讓我與農小英女士開始密切來往,在我參加過她家的一場儀式後,我認她為乾媽,因為這場儀式,我從儀式的觀察者成為儀式的一份子,我也從一個在壯族地區無親無故的研究者,而有了「家人」。2005年的8月,農小英女士請末婆到她家舉行了一場儀式,當時我還住在農村,但因為與她來往密切,所以決心不錯過這場儀式。我本來是以一個儀式觀察者的�身份,想看看儀式組織者的關係網絡。可是到了儀式現場,農女士就讓我把隨身的一個玉鐲子拿下來,然後與她全家(她、大女兒、大女婿與外孫)的衣服放在一起,在儀式中給末婆用來收魂。這意味著我是家中的一份子,才可以參加這個家的儀式。這個鐲子在儀式後三天,就連同其他人的衣服,一起放在一個籃子裡,放在農女士的臥房,三天後才戴回我身上。這場儀式之後,我就認農小英女士為乾媽。不久後我從未婆海芬婆家,搬進了乾媽家。
從以上的描述,末婆的儀式看似為「純」女性的活動,但身為女性的田野工作者究竟有沒有優勢呢?研究者的性別是否會影響研究的成果呢?答案是肯定的。無論男性與女性研究者,都可以參加與觀察末婆的儀式,只不過個人研究生涯不同階段興趣取向的不同,甚至個人的性格特質,會產生不同的研究成果。當然性別界限是存在的,例如一位男性研究者,大概沒有辦法跟末婆共用一張床,但末婆還是能收男性徒弟。在觀察壯族儀式中兩性的互動上,儘管最初意識到末婆的儀式基本上是女人的場子,但進一步觀察後發現男女儀式專家其實有著頻繁的互動,男女兩性在儀式中也是同心協力的分工籌辦與參與。在知識生產上,目前壯族的宗教儀式研究有性別化的趨向,即男性研究男性儀式專家,較女性研究女性儀式專家的比例高。而身為一個田野工作者,我期望與廣西當地的壯族研究者與男女儀式專家共同參與未婆與末公民族誌的生產,朝向「合作式民族誌」的田野工作方式與知識生產,以跳脫研究者自說自話的困境,讓末婆有其獨立與主動「發聲」的機會與管道。
在「性別與人類學知��識」研討會舉辦前一個星期,廣西友人的母親黃丹瑤女士心臟病發去世,我趕去廣西參加她的葬禮,而錯過了研討會。黃女士的驟逝,讓她以前從來不熱衷於各種儀式的孩子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鬼神與靈魂的存在意義,以及通過儀式來維繫生者與死者之間無法割斷的親情的重要性。如果,宗教是處理終極關懷,未婆的儀式就是同時安頓生者與死者的靈魂,以及連繫生者與死者的世界。我特別感謝這十多年來,廣西壯族地區接受我的訪問與觀看儀式的未婆、嬤嬤、娘娘與主辦儀式的家庭與村落,以及任何接受我訪問、叨擾與陪伴我一起成長的壯族朋友們。我的研究如果還有些許的成果,這都是他們的功勞,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突顯出末婆儀式對壯族社會文化延續的重要性。
謹以此文紀念黃丹瑤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