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族裔「飛地」變身為校園「異托邦」
邱韻芳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與社工學士專班主任
其實,「原住民族專班」一直是近代原住民教育歷史長河中的揮之不去幽靈, 如影隨行。此一教育幽靈持續存在的最簡單理由,也許應該可以理解為 「原住民族所需要的教育與其他群體是不一樣的」(浦忠勇 2015:146)
2011年,教育部發了一紙公文,以培育原住民人才為由,鼓勵各大學透過外加名額和獨立招生的方式設立原住民專班。2013年,原民會又祭出了高達百萬的補助計畫[1],火上加油地燃起了全國設立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熱潮。
然而,原專班並不是新的概念。在開頭引言的這篇文章中,浦忠勇把原專班比喻成「教育幽靈」,回溯了它在歷史長河中的飄渺過往--清領時期的「番學堂」、荷西時期的「土番教化」,與日治時期的「蕃童教育所」、「高砂族教育所」 這些其所謂的「類原住民專班」;戰後四、五0年代國民政府陸續開設的「山地簡易�師範班」和「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以及1994年企業家王永慶在長庚護專成立的「原住民護士專班」(浦忠勇 2015:146-147)。至於大學校院裡的原住民專班則是始於2003這一年, 實踐大學和明道大學兩所私立學校先後在觀光學系和精緻農業學系設立了原專班,目標是希望居於弱勢的原住民學生能藉由高等教育來增加知識專業與競爭力(陳誼誠2012:14)。

相較於之前這些零星現身而後又默默散逸的「幽靈」,2011年起教育部和原民會合體推動下的原專班,則是展現了不同以往的蓬勃景象。首先,它以驚人的速度在大學校院裡滋生蔓延。103 學年度時,已有11所大學校開設了15 個原住民專班,這樣的熱潮一直延續到107學年度,每年總招生名額都維持在六、七百名之間[2],且有越來越多的國立大學加入這個戰場。再者,過往的(類)原住民專班主要是作為弱勢族群的補救措施,強化的內容是現代知識,如今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光芒映照之下,原住民文化成為這波大學原專班的課程裡被要求必須具備的元素和亮點。
然而,我們能看到這幾年來原住民大學生人數因專班政策而明顯提高就歡呼讚嘆嗎?對照目前的大學原專班和上述那些已成歷史的原專班,兩者之間是否真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足以使原住民學生從「被扶植的客體」轉化成為「教育的主體」?
這世界永遠不可能如此的單純、美好。
難以被歸類、定位的「原住民專班」
不得不說,從制度的面向來看,浦忠勇用「幽靈」形容原住民專班真是再貼切不過的比喻,因為無論在《原住民族教育法》或大學的組織章程裡, 都尋覓不著它的蹤跡。原住民專班「可能」是原教法裡所定義的「原住民教育班」,但即使是也仍舊輪廓模糊,因為法條中只給出「為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於一般學校中開設之班級」的定義,以及說明「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以利就學,並維護其文化」,並未對所謂「原住民教育班」 之內涵、組織定位多加描述(白紫・武賽亞納 2011:12-13)。
法規的曖昧不明導致學校的組織章程裡無法有原專班容身之處,只能任憑所屬的大學「自主」定義,而後隨意給或不給資源[3]。以我所任教的暨南大學來說,原專班正式的組織定位是「學士學位學程」,隸屬於人文學院,但卻是沒有任何一個校內系所有義務必須支援的獨立學程。成立了一年之後,我軟硬兼施地終於向校方爭取到原專班在各方面能夠比照一個系的待遇,除了教師人數之外[4]。但,教師不足卻是最關鍵的課題。
教育部核准原住民專班成立時,並不會給學校額外的師資員額,而是設想由校內已有的師資來支援。這個前��提對於設在某個系底下的原專班來說問題較小,但會加重系上老師負擔,且很可能並無熟悉「原住民」領域的師資,導致專班的課程往往無自己的主體性;至於像暨大這種設在院之下的原專班,要在目前教學負擔普遍沈重的大學生態中找到願意協助、心有餘力也足的他系老師,更是難上加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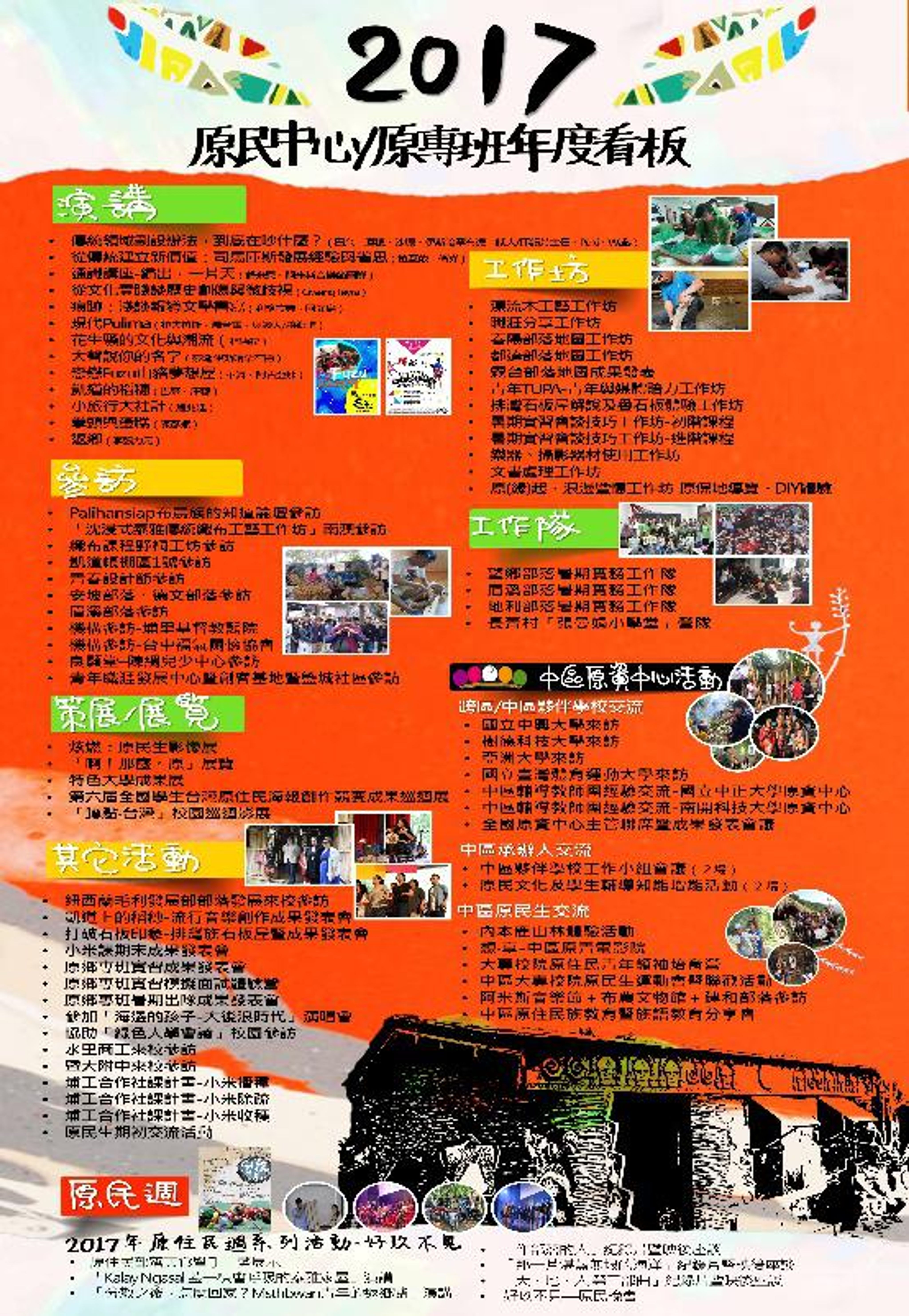
這就是大學原專班所遭逢的真實處境。像是一個系又不是一個真正的系,屬於一般教育,但又需肩負民族教育的使命,教學與輔導任務都比一般科系更艱難、複雜,教育部卻還不給師資員額。原專班成為大學校園裡難以被歸類的存在,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卻被期待擁有能施展魔法的三頭六臂。
那該怎麼辦呢?沒人有解答,每個大學原專班只能各憑本事,努力地對內、 對外尋求資源,用招生成績以及各種亮眼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繼續存活」的價值。
與刻板印象作戰
我不喜歡「原住民專班」這個名稱,除了因為缺乏體制支持外,另一個原因是,它真的很容易被視作原住民學生 「自己自己」的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或誤認為是在職專班,並且被諸多刻板印象緊緊纏繞。
外界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想像,充分體現大社會對原住民常有的一些刻板認知,如原專班的學生應該都很會喝酒、唸書不是重點、常常穿著族服唱歌跳舞等,不僅如此,刻板印象還如影隨形地出現在政府的原專班推動政策之中。早在1999年,高中裡就有原住民專班的設置,而且命名為「原住民藝能班」[5]。在我看來,將原專班定調為「藝能班」乃是政府帶頭將原住民「能歌善舞」,以及「擅長實作但拙於理論」的刻板印象直接植入到制度當中,而這樣的趨向也延續到大學原專班的政策, 差別只是前者明明白白寫在名稱裡, 後者較為隱晦地藏身在相關要點、辦法中。
原民會在民國102年的專班補助計畫中載明,補助類別乃針對原住民傳統樂舞式技藝專班、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專班、原住民專門職業技術專班、原住民觀光餐飲旅遊專班,和原住民農業園藝技術專班;到了105學年度,原民會推薦給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的十個類別則是土木工程、表演藝術、 法律、公共行政、大眾傳播、老年服務類、文創、財政會計、地政、農藝及農經[6]。相較於102年補助計畫而言雖多了不少範疇,但仍是明顯的技藝、應用取向。此外,十個類別中有九個的推薦原因都是現實需求,只有表演藝術類的理由是原住民族充滿音樂、工藝、舞蹈等藝術「天分」。何謂「天分」? 不正是再次肯認了原住民「天生」擅長歌舞的大眾認知?
這些「原住民該是如此或天生如此」的外界「凝視」與政策「定調」透過各種媒介被內化到族人認知之中,成為最難顛覆的心魔。當部落的家長說,「原專班就是要教實用的」或「讓他們有一技之長就好」時,我很難直接開口反駁卻總忍不住在心裡OS,為什麼原住民學生不能學理論、走學術。每年原專班招生口試時,看到來應考的原住民學生裡,十個有九個的興趣是唱歌、跳舞或運動,七個的社團經歷是熱音社或原舞社,我總是很難壓抑心裡複雜的情緒。提到心愛的樂舞或運動時,這些孩子真的好亮眼、好有自信,但是,我多麼希望看到他們談起其他的領域也能如此興致勃勃、閃閃發光。
對抗來自外界和內化在學生認知中的雙重刻板印象,這是四年來我一直努力在作的事,而其中重要的關鍵是,不能讓原專班變成被各種成見築起的圍牆所孤立的「族裔飛地」。所謂的多元文化不該只要求原住民瞭解自己的文化,主流族群卻總是無動於衷,或頂多扮演在台下鼓掌的觀眾。
因此,當我和我的夥伴在暨大校園一步步構建原專班從無到有的版圖時, 同時必須審慎地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設計、和校內其他單位之合作,以及鼓勵學生走出同溫層等各種方式,讓在這個「族群邊界」之內與之外的人有更多一些交流、跨越的機會。盼望透過這些跨界的穿越,讓暨大師生有機會接觸、 認識不同於以往「想像」的原住民,體悟到原住民文化對這土地的意義,而我親愛的原住民學生能夠在找回族群文化的同時,不被束縛地去發展自身潛能,看到眼前無限寬廣的世界。
校園裡的「異托邦」:美麗的無法歸類的獨特存在
那,山頂上的光
好像,要帶領我飛翔
大門取代一道牆,淚眼開了一扇窗
烏雲的背後幻生出了太陽[7]
走過四年的風風雨雨、瘋狂與璀璨,暨大原專班在今年六月誕生了第一屆的畢業生。這真的是一場艱困的生存之戰[8],有太多無法掌控的外力因素,唯一不變的是極大的招生壓力與嚴重不足的師資。我一直透過各種校內、外的場合發聲,希望能從制度的層面去改善、健全原專班的體質,然而,期待能夠和其他科系有同等制度保障的心願卻一再被現實無情地打擊。在某日又一次崩潰的大哭過後,我突然頓悟到, 或許原專班就注定是一個無法預知能存活多久也無法被歸類的存在。如果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那或許我能夠做的就是努力讓它在一回又一回衝撞的過程中長出獨特、不同的美麗姿態, 成為校園裡擁有不同視界與力量的 「異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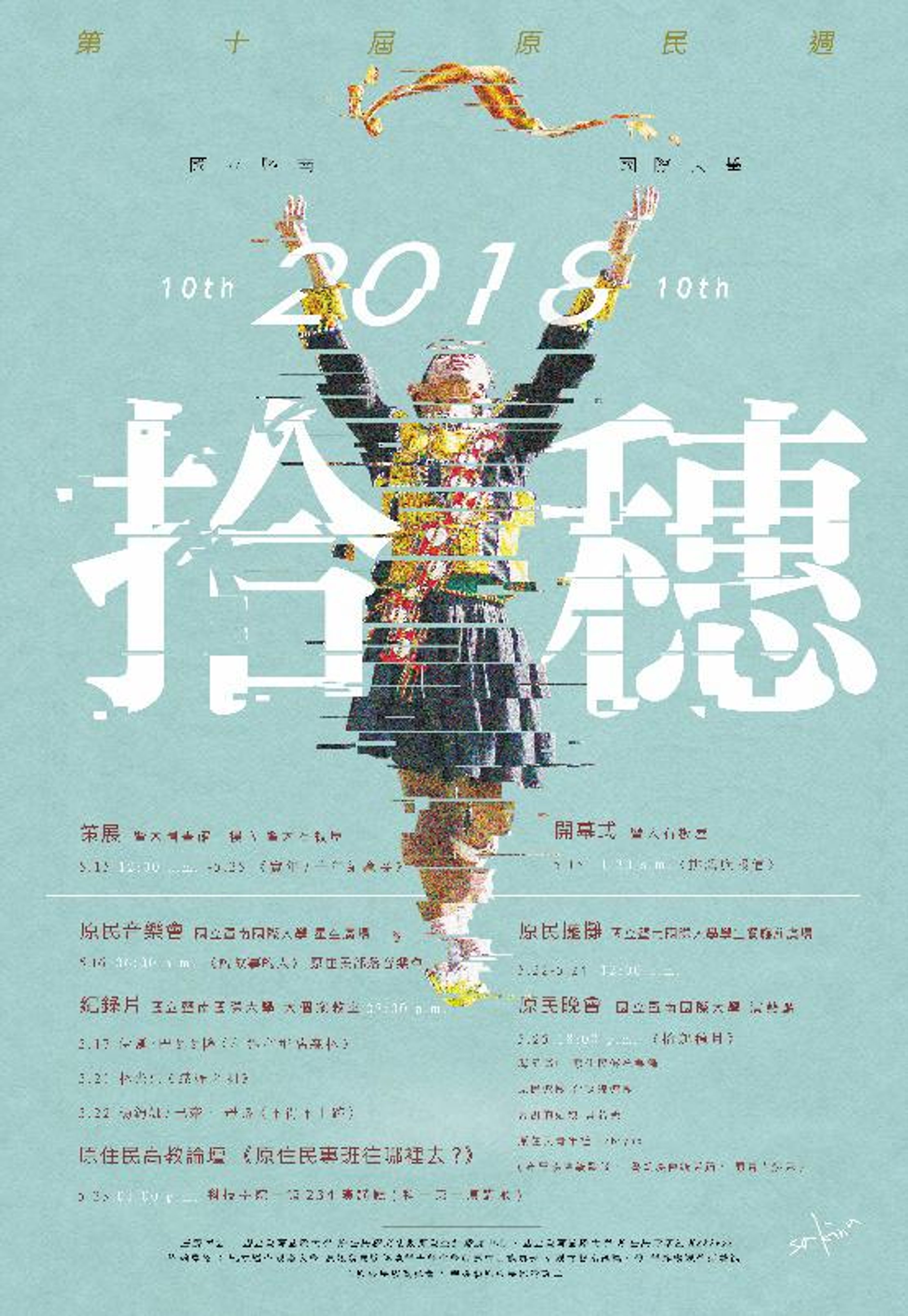
傅柯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出了和「烏托邦」(utopia)做為對比的「異托邦」 (heterotopia)[9]概念。烏托邦是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理想空間,而字根結合了異質性(hetero-)以及空間(-topia) 兩意的「異托邦」,指涉的則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異質空間,人們可透過現實世界與此空間所產生的對比,作為與主流現實對話或對照批評的基石,它就像一面鏡子的存在,在鏡面的虛幻之處,映照真實(簡妙如 2017:234;王志弘 2016:78-79)。
面對沒有穩定制度支持,卻又想給學生兼具專業與原住民文化素養之課程內涵的難題,暨大原專班這幾年來的策略是在近幾年來強調「在地特色」與 「社會實踐」的政策框架之下,透過計畫的撰寫來奮力求生。雖然我們的表現獲得了不少掌聲與經費支持,但過程中我常常忍不住感到質疑,作為所謂的「特色」,原住民文化是否能真正地被校方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抑或只是被當作閃亮的裝飾、補助計畫裡的加分題。而執行計畫時,除了經費之外還有更多的因素必須去考量。2016年年底我們意外獲得教育部一百萬資本門的「聖誕禮物」[10],花了一年時間克服重重阻礙在校園裡搭建了一棟有 「建照」的排灣族石板屋之後, 質疑聲齊來,我必須停下腳步思索文化與脈絡的關係為何,在當代要復振、傳承原住民的「傳統」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路走來,身為原專班成員的我們在向別人說明自己的過程中,摸索著定義自己、建構自己存在的意義,在迷惘困頓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我相信, 只要有足夠的堅持和努力,這力量不僅能強壯自己,也能夠對外散發出燦爛的光芒。
備註:
- 全名為「102 年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專班補助計畫」。不過,第二年(103 學年度)起,此計畫之最高補助金額就從 100 萬陡降為 20 萬。
- 107 學年度則有 16 所大學開設 22 個原住民專班,招生員額共 667 人。本文提到的統計數字皆未將技職體系的原住民專班包含在內。
- 我曾在某場會議中詢問教育部代表有關原專班的組織定位,得到的回應是,這屬於大學自治的範疇,學校要把專班當作系、學程,或兩者都不是,教育部無法干涉。
- 成立的第一年(103 學年度),暨大原專班的師資只有筆者(但員額在東南亞學系)、另一名校內原有的專任老師(需同時負責 NPO 在職碩專班),以及一位新聘專案教師。因招生良好加上極力向校方爭取,於 105 和 106 學年度再分別獲得一個專案教師員額,目前總共是兩位專任老師與三位專案教師。這個師資數在所有大學原專班中已是名列前茅,但和教育部規定大學部一般科系至少要有七位專任師資仍有不小落差。
- 教育部於 1999 年頒佈「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藝能班實施要點」,之後全國有多所高中陸續成立原住民藝能班(林清平 2017:36)。
- 見原民會「105 年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外加比率科系類別建議」,教育部發文轉請各校參採此建議,並專案調高原住民外加名額或開設專班培育。
- 引自蘇打綠的專輯《秋:故事》裡的歌曲 <天天晴朗>。
- 從 105 到 107 學年度的兩年之間,全國新長出了七個學校(八班)的大學原專班,增開名額共 226 名;但同一期間有五個學校(六班)的原專班停止招生,七個學校(九班)減招,總共減少的名額是 245 名。
- 或譯作「異質空間」(參王志弘 2016)
- 請見筆者在芭樂人類學網頁所發表的文章:<在大學校園裡蓋一棟有「建照」的排灣族石板屋>。
引用書目
王志弘
2016 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65:75-105
白紫‧武賽亞納
2011 大學原住民專班學生民族文化教育學習經驗研究─以實踐大學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浦忠勇
2015 學校教育與社會再製大學原住民族專班芻議。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2):145-57
陳誼誠
2012 原班人馬:大學的原住民專班。原教界 45:11-17
簡妙如
2017 由搖滾飛地到異質空間:台北、北京的傳奇 Live House。 傳播、文化與政治6:225-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