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人生的交響曲
王乃雯|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讀博士班以來的這些日子,應該算是我人生中最為顛簸的一段路。
當接到希望能分享博士班生涯育兒的點滴的邀請信時,我心裡既是躊躇也有期盼。猶豫在於這段路的過程,私密性太高,當要成為一種公共書寫時,它的意義究竟何在?但驀然回首,又發現或許不少人,和我當初一樣,在介於「而立」期許與「不惑」之年中,徘徊於博士班的學術路途上。那麼,這些私密語言中的挫折、 困頓、焦慮,就不會僅是我個人生命中的特殊際遇,它仍有著特定的社會結構與時空條件,只是以不同程度的壓抑和強弱不等的意志,展現它形式各異的最終生命樣態。
序曲: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大一、大二時,因緣際會中我參與了兩次在滇東南的田野調查工作,兩次各期數十天的豐富經歷及文化震撼,讓我對這片風土人文複雜多元的土地深深迷戀。也因此,大學��畢業後,我報考了北京大學社會系碩士班以及清華大學人類所,為重新踏上這片土地,尋找正當性。但最終我選擇了非以中國西南研究見長的台大人類系落腳,因為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我墜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戀愛,熱戀中的我決定以台北作為我延續夢想的基地。
但幾年後,隨著碩士論文陷入苦戰,以及是否繼續深造的問題陸續出現,加上各種因素的碰撞,讓師長們曾以為可以長久走下去的我們,陷入長久而痛苦的拉鋸戰。這種錐心之痛,最初來自於我們雙方太希望能替彼此著想,而過度為難了自己。
在這樣的苦楚中,我失去了出國深造所需具備的那份堅定和毅然決然的勇氣,我試著先以國內的博士班作為緩衝,來為彼此爭取更多的時空條件。但最終在兩年多的苦苦掙扎及各方親友的勸告中,我試圖更理性地去釐清我們彼此的問題,然後,帶著無比深刻的祝福,離開了這段感情。而此時,正值我們在一起八年的時間, 當時我已經29歲,在迎向而立之門的面前,這樣的告別充滿了對於未來的惴惴不安。但,也終於第一次勇敢地理清自己的焦慮所在。事後想想,有時我會笑稱這是人生中第一次的「八年抗戰」。
當我在陷入感情低潮時,曾有以過來人身份相勸的學姐,語重心長的和我說如果未來要走在學術的道路上,必須要有以學術為志業的打算,也就是要能犧牲很多東西。但當時的我一直在想,魚與熊掌真的無法兼得嗎?學術的追求與家庭的想望要如何才能取得天平兩端的平衡?
因為在我人生的藍圖中,家庭會是我很重要的一塊拼圖。能全心全力獻身於追求真理,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生命姿態;但投入家庭經營本身的社會歷練,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投身者來說,亦是一種生命經驗的滋養,乃至於反身性關照的另類契機。
決定在29歲真正結束了人生中第一段刻骨銘心感情,既是對於自己學業困境的焦慮,覺得應該要下定決心出國留學;另一方面,在生命歲數中的9似乎有種靈力,對於女生而言,過了29歲,還伴隨的另一重壓力在於理想生育年齡的步步進逼。「成家」與「立業」的兩個擔子挑在身上,對於即將跨越30大關的我來說,一點也不輕鬆。我曾經一度放棄了兩全的夢想,決心去掌握勉強可由自己決定的學業。但各種機緣巧合,老天爺讓我再度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
續曲:偶然中的意識
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之前,其實早已相互知曉彼此十年以上,但十餘年間各自都有不同感情,在一次朋友的結婚宴會中,他偶然的一個小舉措,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男生挺有替人著想的君子風範,而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在隨後的一些場合中,我們知道彼此都仍陷入於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掙扎中。
慢慢地,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境遇,讓我們的話題開始變多,相似的興趣和立場,更加深了我們彼此的交集。而當我正打算準備留學考試的同時,他知道我愛爬山,於是精心策劃了一趟登山旅程,並藉此告白。雖然我沒有馬上答應,但我知道心中那個想要「成家」的慾望又再度被燃起。
然而,我知道以他的家庭境況,他不可能能放下工作和我一起出國,他必須持續工作以償還背負在身的學貸、台北生活的種種開銷還有給家裡的孝親費用。因此,原本已決定慧劍斬情絲的我,再度陷入猶豫之中。 但我想或許我對人生的想像中,一份情感的歸宿還是極度重要,所以我再度因感情放棄了出國求學的計畫,但這也是個艱難的決定。
因為如果未來是以進入臺灣學術界為工作目標的話,繼續在臺灣博士班的學業,將會是一場非常大的挑戰。畢竟,臺灣主流的學術單位,都期待求職者能有資訊和資源相對充沛的國外經歷。所以在這個抉擇的背後,我必須想盡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可以跨越這個約定俗成的門檻,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我將自身的研究重心,從中國西南轉回臺灣,並以具有豐厚文獻背景的稻作農村作為研究對象,藉此實踐跨領域的研究藍圖。
變奏曲: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
我們在一起沒有多久後,距離俗稱高齡產婦的臨界點已日子所剩無多。因此,原先計畫完成學業後再來 「成家生子」的大業,在顧及女性生育年齡的限制,得把相關時程提前。雖然,在生殖科技已高度發達的當下,這樣的顧慮似乎顯得有點杞人憂天。但因為周遭不乏有喜憨兒家庭的接觸下,總覺得還是希望能以保守 (非人工)的方式,給下一代相對安全的前提。但,這樣的時程安排就顯得格外緊張。
我們把婚期排在資格考後數月,本想說這該是權衡各方考量下的較好結果。但一切的意外,總是會在不該出現的時候到來。
在我資格考前半年,先是我們的貓咪小莎因輸尿管結石,緊急手術開刀,好不容易稍微恢復體力,另一隻跟我最親暱的貓咪阿蛋急性腎臟病發,需反覆跑醫院進行點滴治療,在宛如急診室春天的場景中,時常是數小時的煎熬等待。我永遠記得我在進行資格考的當下,心裡還十分焦急掛記著虛弱不已的阿蛋,是否會就此撒手而去。
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在於,我們決定結婚沒多久後,遠在高雄的公公,發現腦部原先不起眼的腫瘤已壓迫到三叉神經,高雄各大教學醫院,都說動刀後,有五成機率可能會癱瘓、變成植物人或直接死亡,我們只能焦急地尋找台北所有可能的資源,好在台北榮總的許醫生成了我們的救命恩人,盡可能解除了這個警報。除了這些糾纏於我們親人的有形病痛,與此同時,娘家父母也因各種緣故,需要我時常回家費心費神的調解許多問題。在如此多頭燃燒的情況下,我們終於辦完了婚禮。 而台北婚宴完的隔日,公公又因開顱術後併發的腦水腫問題,緊急送進台北榮總進行手術,好在手術順利,讓疲於奔命的我們,心中終於放下一塊大石。許多人看我一路走來,都對我說最辛苦的日子已然渡過,一切終將苦盡甘來。
婚後,我用數個月的時間,給了自己一段休養生息的機會,也很順利在成為高齡產婦前,懷上了第一個孩子。但我並沒有就此停下學業的進程,我肚子裡的第一個孩子,陪著我騎著一台破舊的小五十機車,在我博士論文的田野地來回穿梭。整個孕期,這個孩子就隨著縱谷平原的稻子一同生長,直到預產期前一個月,我才返家待產。因此,為了紀念他與縱谷平原這一段特殊的緣分,他的名字裡有著稻禾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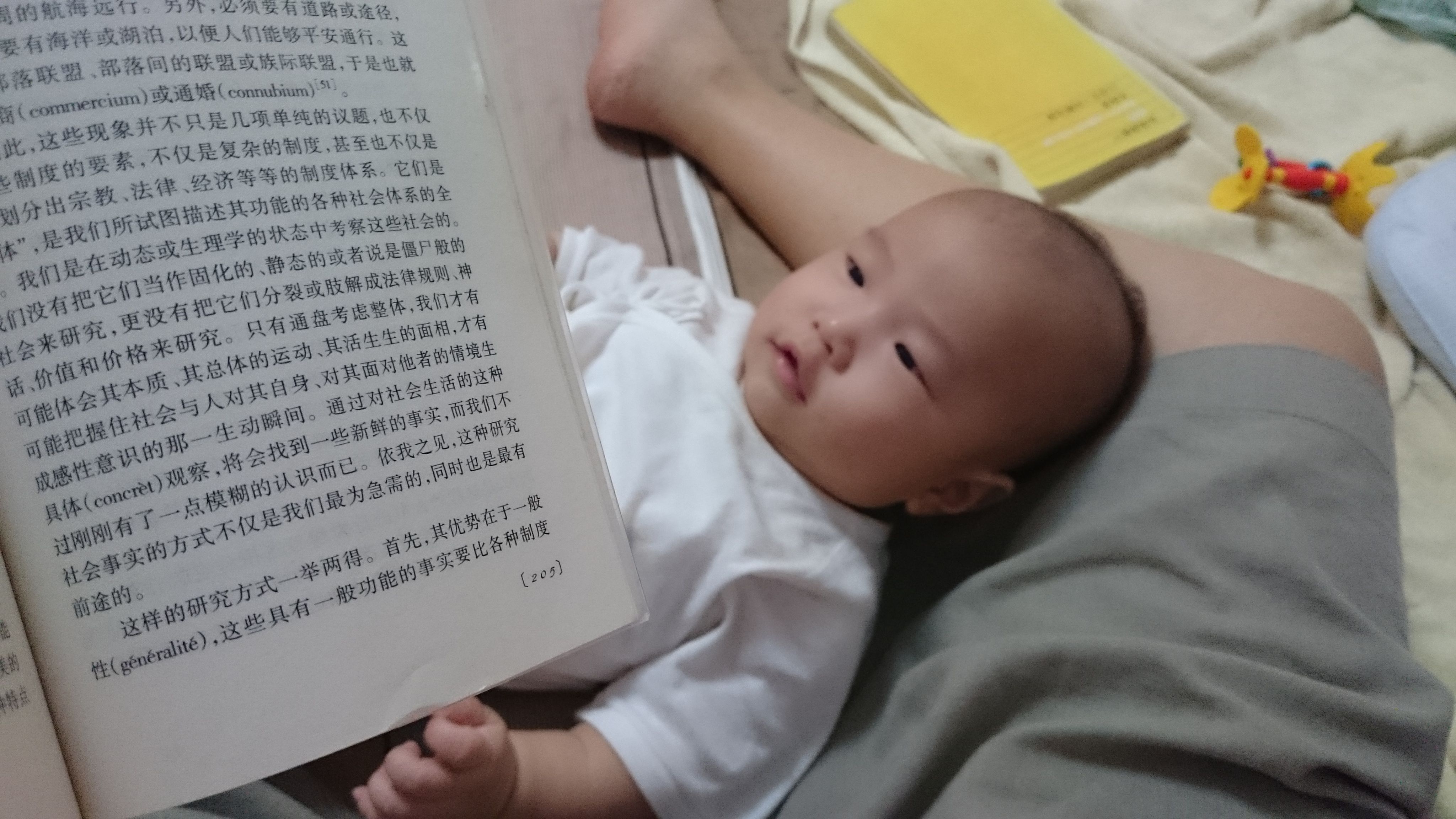
一邊餵母奶一邊剛從月子中心出來備課的媽媽
在還沒有成為母親之前,我一直以為我接下來的路徑會朝向一邊帶孩子、一邊寫論文的方向前進。所以我在生完孩子初期,還非常大膽地繼續想像著我要如何充實自身來彌補無法取得國外學歷的缺憾。因此,我在月子中心時,仍無畏地接下來高中人社資優班的經典導讀教學,並於隨後接下了人類學前輩在大學通識中心所開設的課程;與此同時,還接受了中研院老師的邀請,加入了其研究計畫當中。我天真的以為,帶孩子的彈性空間,可以讓我在夾縫中擠出時間,一邊賺錢貼補家用、 一邊增加各種教學歷練,並且在教學相長的前提下,慢慢推進論文進度。
但隨著孩子越來越大,不再只是個僅有生理需求的嫩嬰時,我開始意識到沒有太多後援的我,除了少數上課時間可委請母親短暫看顧外,我必須緊緊抓住所有可利用的時間,但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我變得非常緊迫, 連帶地影響了我對孩子的態度。孩子在我忙碌的工作中,生長曲線從高標的80%幾,一路掉到低標的15%以下。
我開始積極尋找公托、私托和保母的資源,在老大出生的年代,政府對於育兒補助還非常稀少。我們在公托排到候補100多號,而私托和保母的費用,對於只有一份穩定收入的家庭來說,又顯得十分昂貴,且彼時不斷有各種虐嬰案件發生,對於無法表達的嬰兒來說,我們根本不敢也無力送孩子進入這樣的系統。所以我決定放下論文進度,專心於教學和好好帶著孩子長大。
我每天帶著孩子流連於台北各大親子館、圖書館和公園,善用所有的公共資源,下午在返家時的路上,趁孩子在嬰兒車上午睡時,我推著嬰兒車,一邊行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一邊思考著論文的可能方向。
孩子滿兩歲後,我們終於多了一種幼兒園的選擇, 比起托嬰中心,幼兒園的收費會比較平價一些,孩子也具備了一些語言表達能力,我們也可稍微放心一點。但家附近的幼兒園幾乎都沒有設置兩歲幼幼班,而儘管已開始有新設立的非營利幼兒園,但我們的籤運仍然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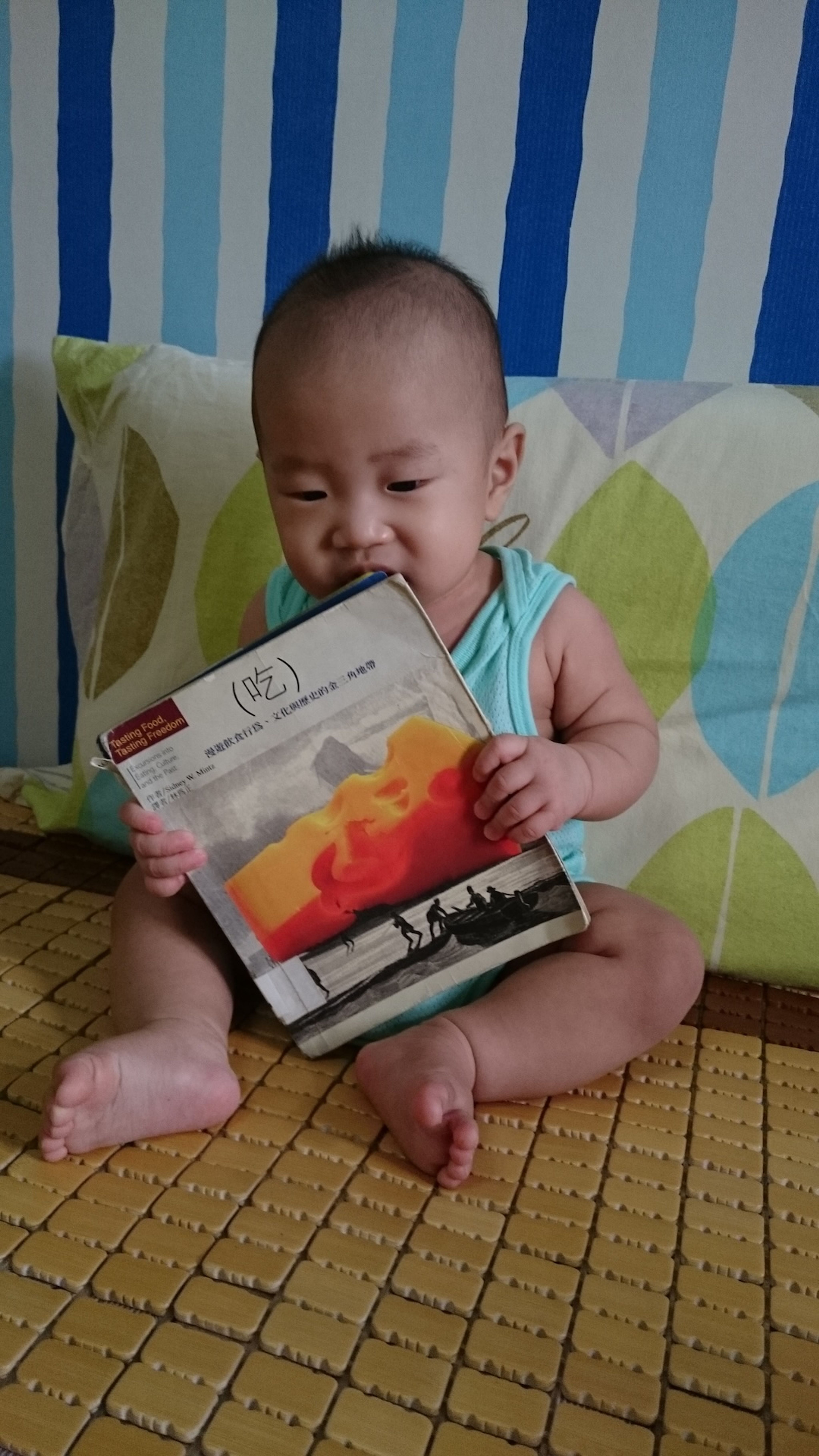
一書二吃中的媽媽與小孩
好在孩子的父親因在有設立非營利幼兒園的公家單位就職,幸運地被我們取得一席名額,但也讓才兩歲多的孩子,開啟了艱辛的求學之路。每天早上他不但得趕早準時起床,還得與爸爸一起擠十幾站的捷運才能到達學校。而第一次上學的孩子,在適應困難下,我也陪著一起上下學了一個多月。
好不容易,九月下旬孩子在學校稍微進入狀況,但好景不常,當年的十二月,我的父親因腦溢血而病倒。 父親向來自負與堅強,在生命中的各種挫折他都以無比的意志,走過一重又一重的困境。但這次襲擊父親的, 不是來自外在的攻擊,而是他自己的身體;更糟糕的是,還是作為身體總司令的大腦。
我陪著父親艱難地從術後的失能中,反覆緩步走在醫院的長廊復健,好幾次在他有長足的進步之時,卻受到感染的襲擊而發燒,又只能打回重練。然而,更讓我覺得辛酸的是,面對父親受創的大腦,時而清醒、時而迷糊,我開始困惑於我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鼓舞病榻中的父親,請他再次以堅毅的精神,勇敢面對老天爺給出的一手爛牌。面對父親的驟變與難以捉摸,另一端即將滿三歲的孩子正以驚人的爆發力展現他對世界的認知, 這讓我感受到了無比的喜悅與驚艷。
在反覆輾轉於各大醫院復健的日子終告尾聲後,父親回家後曾有段相對平穩的日子。我們也開始面臨是否要有第二胎的慎重考慮,因為那畢竟是我們對一個完整家庭的想像。而我與姐姐之間的親密情誼,也讓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個手足在人生路上相伴。此時,我的年紀已往「不惑」大關邁進,而我先生大我四歲,也考量未來孩子出生後,是否還有能力和體力照顧他。但父親的病況以及我那遲遲無法完成的論文,始終讓我難以大刀闊斧的做出任何決定。於是,在百般糾結中我們決定放手一試,看天意如何決定。老天爺也在我們第二次嘗試之時,就給予了明確的答案,我懷上了第二個孩子,而且是我們盼望的女孩。
但好景不常,父親的病情在我懷胎三月時,突然急轉直下,後來才知道除了腦溢血的問題外,癌細胞也早已侵襲他的肺部,沒多久,我就帶著肚子裡四個月大的孩子,於溽暑的盛夏八月,在火葬場叩別了父親。隨後便一路忙著幫父親張羅著一個月後的追思會事宜。
然而,在我懷胎七個月時,我突然意外出血,此時的出血非常不尋常,找遍三位婦產科名醫都有各自說法,而且判斷南轅北轍。但最糟糕的後果是,小孩有可能會面臨極度早產。因此,我最後選擇遵照了最保守的作法就是吃藥躺床安胎。
於是在孩子出生前的最後三個月,我除了吃飯和洗澡,都是「躺平」狀態。但對於一事無成的焦慮,促使我努力把我所欣賞的老師在youtube上的所有演講全部聽完,搜尋所有與論文相關的節目、演講與資訊,讓耳朵非常認真工作了近三個月,就這樣苦苦終於熬到差點又過了預產期。但至少,孩子沒有早產,平安健康的來到這個世界,一切的辛苦在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間百感交集,但也值得了!
孩子出生的那時,外在的世界並不平靜,臺灣正逢新冠肺炎全面擴散的初期,而二月出生的孩子,到了五月左右全臺灣進入三級緊戒狀態,所有的人都被迫關在家裡長達數月。
哥哥雖已是相對懂事的小孩,但面對疫情的反覆無常,成天待在家裡,小孩過多的精力無處發洩,加上他剛從獨生子狀態成為哥哥,還有很多需要適應調整的地方,我必須一個人在家獨自面對兩個小孩。

三級緊戒只能在家玩貓的妹妹
隨著天氣益發炎熱,辛苦指數也倍增。我開始經常性的頭痛欲裂,最初我以為這是疲憊加上長期壓抑造成的。幾次進出急診,醫生也說可能如此,便開了許多放鬆的藥物給我,但殊不知此時已是老天爺決定給出人生另一道考題的暗示。
變奏曲: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
在12月初的某天,我和母親相約借她的車,順路去買嬰兒用品,她看我臉色慘白,聲音虛弱,堅持要我再次進急診瞭解狀況。碰巧的是,當日急診醫生的同事, 數日前同樣因為急性頭痛但不幸過世,所以他高度懷疑我可能也有腦瘤的問題。結果在急診進行初步的檢查之後,證實了他的想法,我腦中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腫瘤壓迫著我,導致了我的虛弱。由於腫瘤已經相當大,他建議馬上轉往大型教學醫院進行手術。
在我的堅持下,深夜中,我被緊急轉送台北榮總, 母親焦急地為我尋找許醫生,希望能為我這個尚在哺乳的媽媽,進行這個重大手術。我在急診室等候了一天一夜,終於得到許醫生的首肯,轉進了準備開刀的病房, 而當時,我還得一邊趕緊用藥把母乳停掉,以免因發燒引起額外的事端。混亂中,我根本忘記了害怕。
在歷經漫長的十多個小時手術後,我被轉進了神經外科的加護病房,在麻醉逐漸退去後,逐漸清醒的我, 眼淚終於第一次忍不住掉下來。
想著當年父親是怎樣經歷了這一切,而他卻最終沒有能回到那個原來的自己,而我幸運地在許醫生的協助下,能繼續��守護著我摯愛的孩子長大。在冷冽的冬天, 疫情依然肆虐,剛動完大刀的我,虛弱地不適合接種疫苗。

媽媽太忙派出哥哥餵飯XD
所以在身體的狀況稍稍好轉之後,我開始以中醫的方式來調理,一邊慢慢嘗試著、摸索著該如何重新走上一條可以繼續前行的路。我開始閱讀著先前想看的一些書,但不太過勉強自己,逐漸地我發現這些年來在生命這堂課中我累積了許許多多能量,雖然它們都是以各式各樣的挫折形式出現,但我發現,那些年我推著嬰兒車在大街小巷的思考、在面對生命傾頹與迸發的探問、在決定留下時所做得一切準備,或多或少、涓滴成河般地給予了我意想不到的養分,它們的滋味並不一定都好, 但或許正因五味雜成,才有其獨特的力量,才能讓我作為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在面對形形色色的生命故事和人群處境時,可以重新有了不同高度的視野!
這篇文章,雖然高度私密與個人,但呈現了臺灣青壯世代的學術從業者,所面臨的種種結構困境,包括缺乏合理��的獎助學金資源與友善的育兒制度對待。近年來,這些項目在許多人的倡議下,已有逐漸改善的趨勢。延續此一精神,期望透過這樣的書寫,除能持續推動更為友善的育兒時空條件,也能稍稍撫慰那些在學術之路上遭遇親職困頓的不知名伙伴。我想也唯有如此, 這個書寫中那層隱晦的公共意涵才能有其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