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脆階段中的戰鬥親職
卓浩右|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級研究員
其實這是一篇定位不明的文章[1]。一開始我想寫篇勸世文,提醒所有跟我一樣——身處博後階段、不是沙文主義者、認為分擔家務和育兒勞動天經地義是份內之事的異性戀男性,如果你跟伴侶起心動念想在這個階段生小孩,但沒有辦法滿足我在文末條列的那些可能會讓你不滅頂的條件的話,我會建議你最好不要生。
但因為生小孩以及陪伴小孩成長本身對於豐富自我的生命經驗這種事情又幾乎是無可替代的,並且靈長類動物本來就有生育年限的物理限制擺在眼前,因此如果真的決定無論如何都想要完成人口替代率,那請把這篇文章當成某種不保證有效的生存手冊。一些年後的讀者如果不小心看到這篇文章,建議去google一下看看我是否有上岸,有的話就當成生存手冊,沒有的話就當成失敗的案例作為參考。以下正文開始。
根據國科會人社中心在2023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 (Citation),多數研究所畢業後的博士都需要面臨為期平��均六年左右的不穩定工作的職涯階段。六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不論性別,對於需要較久的時間完成學業的人社博士來說,都是一個尷尬的時段。一方面,人社博士畢業時往往都已經三十好幾甚至快要四十歲了,如果沒有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結婚生子,畢業之後才來決定要生小孩會面對時間無多的壓力。另一方面, 當前的教職競爭激烈且僧多粥少,即便是正式教職前被視為過渡型職缺的博士級研究員也往往一位難求。
也因為如此,新科博士往往被期待要把自己所有的學術能量在短期內完全燃燒,讓前輩學者們看到一顆炙熱的新星正在閃耀。於是許多人社博士甫一畢業,就發現自己面對了重大的選擇:是否要生小孩?現在就生還是上岸(找到教職的俗稱)再生?
2019年8月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的我,馬上就面對了上述的這些問題(還要再加一個2019畢業限定的武漢肺炎所帶來的全球就業市場的衝擊)。在畢業後的頭幾年,原本的規劃是要先全力衝刺拼上岸,等上岸之後再來生小孩,雖然一樣會有接踵而來的升等壓力,但至少經濟上會有穩定收入比較不用有斷炊的憂慮。不過隨著幾次的事與願違、發現上岸這件事情似乎看不到盡頭之後,和伴侶討論完決定不再繼續等待了,於是在2022 年末,我們家多了一位新成員。用不了多久,我就很快的發現,原本已經是困難級的求職之路瞬間就變成了地獄級的挑戰了。
挑戰的首先,當然是生活作息大亂、睡眠時間破碎且大幅減少還有各種手忙腳亂。奶瓶沒裝好以為小孩都喝進去了但其實都��餵給了衣服、戒慎恐懼的扶好脖子拍嗝以為成功了卻發現連剛剛餵的奶都一起拍了一地、就不要說那些自以為穿好了的尿布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諸如此類的混亂無關學術生涯,大約是每位新手父母必經之路,然後在洗不完的奶瓶中,提醒著初為人父的我,生活的重心要開始有重大的轉變了。
在有了小孩之後對於學術之路最大的影響,我覺得是在於作息與睡眠。雖然我相信學界中一定存在那種真正厲害的研究者,可以非常妥善的利用每一段破碎的時間,不用熱機直接開工的真正強者,但很遺憾的我不是。在我過去上過的每一堂關於寫作的課程中都強調規律的作息:「找一個永遠不會有人打擾你的40分鐘,那就是你最好的寫作時間,不管它是清晨還是黑夜,就是那段時間。」當年寫作課老師的金句言猶在耳,有了小孩之後發現馬上不可行。新生兒在六個月大之前每三個小時要喝一次奶,餵完之後還有哄睡、拍嗝、換尿布洗奶瓶等等的任務要完成。
等到這些都完成之後稍微喘一下,也差不多要開始下一個循環。當然,一天6-8次的奶是夫妻兩人共同分擔,但被切碎的時間和睡眠卻顯著的影響了工作時的表現。我需要更多的時間進入寫作狀態但能夠專注的時間卻比過去更為短暫;隨時都在想睡覺的狀態也嚴重的影響了寫作的進度和品質。當然,我還是相信學界有神人可以在這種一天也許睡的到五小時但其實是五個一小時的狀態下有規律的產出,但可惜我就只是個光維持清醒就耗盡了氣力的凡人。
畢竟是學人類學的,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一��點民族誌細節讀者大概會覺得我在唬爛,一定都是你太太起床顧小孩你都在旁邊呼呼大睡。但因為我的伴侶是位高校教師,不像我工作和起床時間可以相對有彈性,所以在她育嬰假結束後有段體感超過一世紀的幾個月中是我負責深夜的突發事件。半歲嬰兒的睡眠習慣尚未建立之際, 一個晚上醒來六七八九次純屬日常。
帶過嬰兒的讀者即使忘了或者不想想起來,心中應該都還有個埋藏甚深的記憶在告訴你每當碰到這種嬰兒忽然暴哭坐起的深夜裡,你只有不到一分鐘的黃金時間可以安撫他把他重新放倒而你也可以假裝自己沒有醒來過睡眠沒有中斷的睡回去。一旦超過了那一分鐘,小孩完全清醒了之後要再重新哄睡回去就可能是一兩個小時的事情了。而更常發生的是當你精疲力竭的把小孩重新哄睡了,也差不多該起床餵他喝奶了。印象中在那段時間中,每次起床都覺得自己的血管、腦袋還有可能的學術生涯都又更危脆了些。
當小孩差不多半歲大之後,幸運的抽到了公托,本以為接下來的日子可以比前半年要來的好些而也的確好了一些,但就一些。白天開始有了較多的時間可以工作,感覺一切就要重新回到正軌,至少重建工作節奏開始成為可能。然而這時又出現了新的挑戰:生病和停課。人之初接的不是性本善而是必生病,對於新生兒來說,公托是第一個長期接觸大量照顧者以外人類的場合,大家交換病毒建立免疫系統也是人生必經之路。
發燒、咳嗽、呼吸道感染幾乎是小兒日常的光景; 剛開始送托時每週至少有兩天會在下午接回小孩後直奔兒科診所,等到回家再次打開電腦往往已經十點之後。 不過這些都還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停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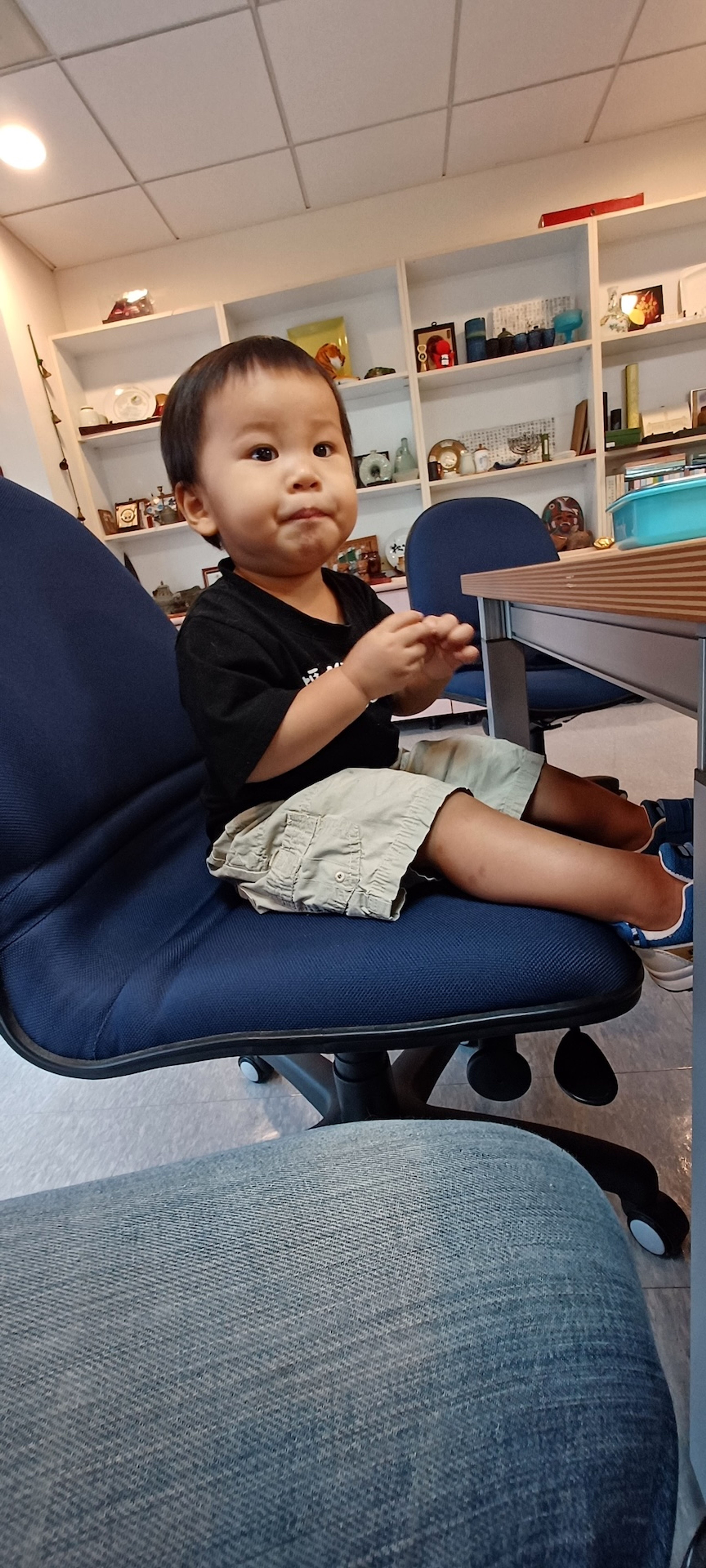
腸病毒停課跟來社會所開會
自2020年開始,似乎是因為當時大流行的腸病毒是容易讓小朋友發生重症的病毒類型,因此疾管署制訂了相當嚴格的停課標準。在同一週內一班當中有兩名學童感染腸病毒則該班停課七天。在保護小孩的健康安全為由所制訂的這個停課標準乍看之下立意良善,不過實際執行起來卻會發現可能會對家長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在小孩停課七天時家長得請家庭照顧假,不過家庭照顧假不止無薪且一年最多七天。換言之,在沒有外援的狀況下,一個核心家庭大約只能負擔一年最多兩次的腸病毒停課,並且是要在父母都能無礙的請家庭照顧假的條件下才得以成立。設若停課次數超過兩次,那麼家長必須要不就是請特休,不然就是找外援;如果兩者皆沒有,就要自己想辦法。
在相對城市的區��域或者可以找到日托協助,不過由於腸病毒的停課往往是當日通知當日停課,而日托通常都要至少前一天先預訂而且還常常訂不到。在完全沒有配套措施的狀況下,唯一的可能就是父母中的某一人放下手邊的工作來照顧不一定有得腸病毒但一樣要停課的小朋友,七天。說了這麼多,我發現我似乎還沒跟大家說我去年(2024)一整年碰過幾次腸病毒停課?其實不多,就九次。
九次停課等於一年有當中有兩個月又一週的時間小朋友沒有辦法去公托,家長必須要在這段時間負起全時照顧的責任。對於高教產業中的勞動者來說,這時就會陷入一個兩難困境。因為工作往往具有時間上的彈性, 所以當這種突發事件發生時就會成為第一線扛起照顧責任的人。兩歲的小孩又正好處於開始有行動能力但什麼都做不好,還很有可能在嘗試任何一個簡單動作卻失敗時輕則生氣哭鬧,重則跌倒受傷的時期;因此,一旦肩負起照顧的責任幾乎等同於所有的工作都必須要暫停, 把注意力都放在小朋友身上確保他們可以活著回到公托。

在職涯尚不穩定的階段開始育兒雖然辛苦 但還是有許多美好時刻,比如說這種景色
也許有讀者會覺得難道沒有什麼可以一邊工作一邊顧小孩的方法嗎?相信我,我試過念Guy Standing的不穩定無產階級給兩歲小兒聽,換來的結果是我需要買一本新的。育兒跟學術積累就是這麼樸實無華的彼此打架,而一旦腸病毒發生,育兒這邊永遠都是獲勝的那一方。不過,腸病毒可以讓公托停課,卻不會讓新手爸爸眼前的死線一併停止。小孩要顧的同時死線還是要跨過。於是,在沒有其他辦法的狀況下,就只能白天顧小孩,等小孩睡著之後再繼續工作到眼睛張不開為止。
在Kmec (2011)以及其他眾多關於母職懲罰和父職紅利的討論中均曾經提到,有小孩這件事情對於母親和父親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即便在工作上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表現,但是有小孩的父親往往會因為有小孩而得到更多的優勢,不論是加薪或者升遷的速度都會比母親來的更快。
因此,母職成為一種對於女性的懲罰但父職卻成為男性的紅利。這類的研究在當代已經成為人們理解職場性別不平等的背景知識;為了消弭這種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臺灣雖然腳步不算快但多年來也陸續有許多的措施試圖讓女性不會因為生育而在職場上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高教產業亦不例外,近年來國科會對於女性研究者都有多項生育相關的支持措施。比如說給予懷孕到有三歲以內小孩的女性研究者每年一件研究計畫隨到隨審的機會;或者已有計畫者可以追加一位研究助理和博士後的人力幫助�。這些政策上的支持對於女性研究者在同時進行研究服務教學和育兒的時候多多少少能夠得到一些幫助,絕對是立意良善且有實質效果的政策這點無庸置疑。
然而,如果繼續看下去,會發現雖然國科會對於男性也有生育補助措施,但卻只有「留職停薪育兒」和 「單親獨自育兒」的男性計畫主持人才符合上述因為育兒而得到的政策支持。換言之,這樣的政策設計其實暗示著男性研究者「通常」不需要照顧小孩,因此只有在確認男性研究者一定要照顧小孩的狀況下,才能夠申請補助。
當然,從關於臺灣社會的許多研究中可以看的出來,國科會這樣的政策設計其來有自;在臺灣,家務勞動和育兒照顧的責任,不論階級和職業主要還是落在女性的身上。因此這樣的政策設計的確就制度上來說能夠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狀況。然而,隨著性別意識的抬頭, 其實也有越來越多的男性不再只是「幫忙」家務,「協助」照顧小孩;而是把家務勞動和育兒照顧責任視為義務,是自己身上理所當然的承擔。

腸病毒停課的標準狀態-在背上
對於這些男性來說,在實踐家內性別平等的同時, 其實很可能會替他們自己創造出相當不利的狀態。因為這個社會上依舊預設了男性不是主要照顧者,不是家務勞動的承擔者,依舊是那個在可以在職場上百分百配合和輸出的「理想勞動者」(Acker, 1990)。換言之,只要在學界中依舊存在著男性是不需要或者少部分承擔家務勞動和育兒照顧工作的刻板印象,那麼男性研究者如果真的願意承擔這些責任的時候,這樣的顧家形象並不會真的創造什麼職涯紅利,反而會因為育兒任務的時間需求和特性吃掉大量工作時間與精力,從而讓原本就已經很困難的求職任務變成地獄級的困頓。但反過來說,這不就是大部分的女性研究者長期以來都在面對的處境?
不過,這種混亂狀態至今也兩年了,生命自會找到出路而我也的確找到了一些正在實驗中的作法,看看能不能在同時承擔育兒責任的時候繼續維持高能產出卻不會減壽太多。
比如說拋棄過去那種一定要有進入儀式的寫作迷思,打開檔案就寫。盡可能的將家務勞動和育兒責任的時間合併,比如說趁著小孩自己進食的時候把可以洗的東西都洗完;準備伙食的時候就不要太講究大菜什麼的,方便迅速的食材才是正辦,能夠剁兩刀搞定的青菜就不要剁三刀,需要抽絲剝繭的地瓜葉一類就等以後有時間再說,諸如此類看似細微的地方都能幫助新手爸爸省下不少時間。比如說能夠找外援時就絕對不要害羞開口,過去自己和伴侶都是不太喜歡尋求外援的人因此碰到停課�時都是儘量能夠自己來就自己來,直到去年下半年兩個月小孩只去了公托16天,真的受不了之後才開始尋求外援,然後發現有幫手真的差很多。
最後,還是稍微總結一下,對於一位正在求職並且認為育兒和家務勞動是份內之事的男性研究者來說,如果不是真的很喜歡小孩而且有迫切的覺得現在立刻馬上要有一個小孩出生,那麼我會建議先不要。雖然我也需要強調,有了小孩之後雖然身體上會立刻變的很疲憊, 但是生活中也會因為小孩的出現而多了很多的喜悅。
許多時候不論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回到家裡看到那個純粹喜悅的笑容就會覺得似乎一切都沒什麼問題,生活還是可以繼續前進;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在博士後這個階段生養小孩,的確會讓原本就已經很危脆的職涯變的更危脆,在做這個決定之前不可不慎。
如果真的有強烈的動機想要在這個階段生小孩的話,那麼也許你會想要考慮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再來放心生養:
1.有強大的外援體系
2.伴侶要有穩定工作
3.自己的心臟血管很健康
4.在一天只睡三小時的情況下還可以操作腦袋有穩定產出
如果覺得上述這些條件不是問題,那就放心生小孩吧!

某次停課時白天帶去賣場買菜
參考文獻: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 society, 4(2), 139-158.
Kmec, J. A. (2011). Are motherhood penalties and fatherhood bonuses warranted? Comparing pro-work behaviors and conditions of mothers, fathers, and non-paren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2), 444-459.
備註:
[1]本文以具名形式通過伴侶審查,所言字字屬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