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子偕行?移動跨境中的學術追趕與親職戰鬥
黃舒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與子偕行」是多美麗的一句話,然而當「移動」是在學術工作中已成必要一環的跨境會議和移地研究,且連結上「國際化」這項高教重要指標,「移動重擔 (mobility burden)」 Urry (2007, p. 336)是特別挑戰的一項,讓身旁有十二歲以下幼小孩童的學術工作者,不得不在學術專業呈現、交流效率、孩童主體期待、金錢、時間等等因素中掙扎不斷。
「如果能一起到異地感受學習,開會之餘還能拉著小手一起散步、異地寓教於樂,想來多麼美好?」但移動中真得能樣樣都要嗎(have it all)?倒退百步問,多帶一個小孩出門,真得能順暢地過關抵達會議室嗎?研究及教學國際化相關的工作,往往在執行前兩年即開始規劃、部署經費來源,強調長期穩定性,往往和充滿變化不定的親職(面對小獸,我們甚至難以掌握接下來一兩個小時的狀況!)在本質上是矛盾的。肩挑學術/親職人在其中,時而在長期工作承諾和即時應變中錯亂。
國際會議中的同儕互相carry
小孩四歲以前,有特別緊張的兩次,一回是懷孕前即規劃的日本東北移地教學,需要離開兩週,當時我非常幸運地,因適逢伴侶請育嬰假期間,還有婆婆支援, 四個月大的小孩還沒有太多言語情感索求,我依依不捨但還不需太煩惱;而後是在她剛滿一歲時需要出席香港 ,沒想到出發前一夜小孩開始發燒,隔天早上還是依原計畫去到了機場,但自己心裡過不去,一再電話確認溫度是否將降下,心心念念之下,在櫃檯放棄登機,厚顏請求慢一天與會(已顧不得是否讓負責招待的主辦方學校留下不專業的印象),多花了24小時確認情況好轉,更改班機翌日再出發。
以上這兩次已精疲力盡,本來很擔心要如何繼續度過嬰幼期,沒想到一場全球大疫,在小孩二歲至五歲的階段,國際會議和移地研究等停擺至少三年(2020/3-2022/12),遂避開了需擔心移動性和親職衝突的焦慮, 反正全球都不能輕易跨界移動。
回想當時,困頓中卻偶有輕鬆感受,甚至和學界朋友半開玩笑地比較起彼此如何在鏡頭之外展現三頭六臂的特技,甚至有人宣稱能一面遠距上課、一面給小孩換尿布。好幾場次的跨時區會議,熄燈拍哄小孩入睡,自己則帶著藍芽耳機努力不要睡著。總之,那三年因疫情的靜止,反而延後面對了隨身親職移動中不易的挑戰。 那三年亦格外感覺到有同理心支持著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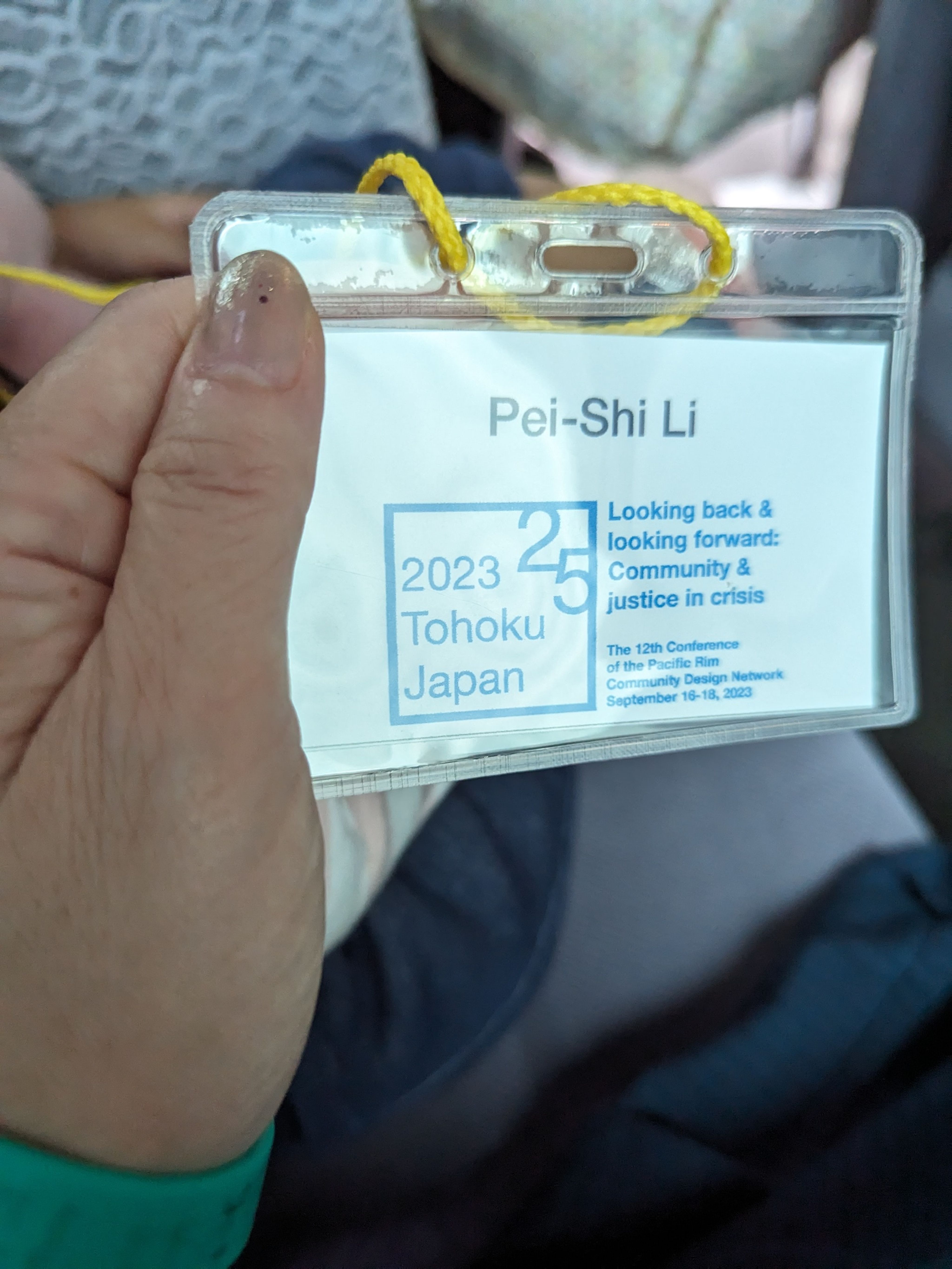
在日本仙台市的東北大學參加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雙年會
會議方很友善地給小人們也做了名牌,大大提升她們的參與感
2024年夏季的研討會(AAS-in-Asia)來到日惹,多要感謝布朗大學的人類學者朋友蘿倫,前一年在韓國大邱的會議結束後,就超前部署建議,來年去到日惹,不如一起租一間Villa共享吧?蘿倫自己是一個兩歲半小男孩提米的媽媽,來自加州的她恰好就是以印尼襲產為田野,而且她田野中結識的人生伴侶是印尼人,亦是難得投入參與照顧的一位。有此約定,我才沒有(太多)擔憂地帶著小女孩同行-私心也想突破她的行旅舒適圈, 看看日韓之外的多樣地理文化。
也就是說,移動仍可行,但需要事前細心籌劃調度資源到位。同儕蘿倫的印尼伴侶剛好是自營事業負責人 - 不代表他不需要工作,只是有更多彈性安排管理工��作。這幾天看到的是,他一面陪著孩子們玩,不時也掛著耳機,隨時回應公司狀況。
除了友情互助,還需要都市型態、空間關係和設施來支持啊。其他國家同儕聽聞了我們這次的安排就無奈地說:如果會議是在倫敦或都柏林,甚至是台北,應該都不易以可負擔的價格得到同等舒適的安排吧?

韓國大邱的AASinAsia會議場外她抱怨說還要開會多久呢
共居的好處是,親職在身的我們可以多少輪流參加會議場次,分攤照護、獲得喘息。小孩也樂得不需要跟我們去到太乾燥無趣的校園會場,在「家」裏有她們的天地。另一個重點是,小孩們一起玩,而非落單狀態,也減少了大人的負擔。我後來才知道,在那幾天,原來五歲小女孩也幫了些忙,身為穆斯林的印尼爸爸每日需定時走開禱告,在那段時間,我們家小女孩就化身照護者,幫忙看護三歲的小弟弟,她也順便建立了對於穆斯林信仰慣習的認識。
會議期間共居還有一點同理壓力分攤的可能,例如,小孩睡著後,我輕手輕腳到起居室準備完成未竟工作和信件回覆,不到五分鐘後發現蘿倫也出來了。會心一笑中的同理是無奈和偷得時間的一點點幸福(如同一篇文章生動的題目:Smith-Carrier et al. (2016)共筆“My only solution is to work later and sleep less”),其實我們沒有餘力去想自己是不是工作狂,但能這樣照面彼此的「勉強」(同時指涉中文意義和日文漢字意義),本身似乎就有某種療癒效果。
然而還是要說,在一年至少四五回的移地會議行程中,能有一至兩回兼顧親職,已經是太幸運奢侈的。先不說別的,研究計畫或邀請方能支持的旅費一貫是不包括隨行親屬的。
海外研究休假不輕鬆
身為大學教師,有個珍貴奢侈的機制名為「研究休假」,好進行充電、研修精進。每連續教學七年一次可休息一年,或是每三年半可休息半年。在臺灣的學者們多會利用這段時間到國外進行研究休假,一方面拜訪維繫相關系所學術網路,一方面進行需要靜心推進的工作,例如寫書、寫作準備大型計畫。
而這行之有年的機制並沒有考慮親職太多。存在於學界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性別歧視-如果恰好是育兒階段的女性研究人員,那剛好可以藉著「研究休假」好好帶小孩吧。換句話說,沒有人認真看待這個階段的女性研究人員能利用研究休假而有任何成果。
更慘地是,如美國學者Lawless的境遇,不巧在研究休假期間發生了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而造成的百業暫停、居家隔離政策,幼兒突然回到了她膝上(“The baby is set on my lap." Lawless, 2021),她的研究休假被瞬間取消,成為旁人認知理所當然的家庭主婦[2]。
學校教務可以休假,但親職難以休假切分,怎麼安排?不僅是進行各種安排是需要資源支持,還要克服自己心裡是否能輕易卸下親職。難為在於,即便可以理論分析,親職應該共同承擔,但「親職」其實不只是工作,還是難以完全停下的親密關係,難以完全分擔或外包。
在2024年初開始規劃研究休假要到東大訪問時,我開始感受到這個議題的困難。給自己張羅訪問所需的文件安排已經繁瑣,遇到了東大學人住宿網頁上明言不能接受五歲以上的小孩同住時,我大受打擊。「這是什麼規定?」我幾乎要放棄學校宿舍而另覓校外住宿時,接待我的學者阿古智子老師來信說,他們非正式地說可以,妳就放心來吧。我至今還不完全明白這則規定怎麼可以存在於號稱要積極重視兒童福祉、少子化議題的進步國家中。
住宿問題只是眾多課題中的一環。另外還有就學課題。我想了幾種方案,正準備和另一半討論,沒想到他輕鬆(草率)地根本不想討論:妳就自己去東京,讓小孩留在臺灣吧?我滿是挫折,同時也認真思考起來,為什麼自己不能放棄、為什麼心裡過不去。
社會學名著《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指出了親職勞動是無償�勞動的合理化、自然化,以「第二輪班」概念化探討,在親職伴侶雙方都有工作的狀況下, 妻子下班之後未必能真正休息,還會花更多時間處理家務照顧(例如育兒或照護長輩)。許多社會學研究統計持續在比較親職雙方的投入差別(例如,男性與女性的家務時數比較)。
幾年來我真正感受到的是,其實不完全是時數的問題,而是親職是沒有下班起迄的、如影隨形的生命邏輯。「第二輪班」受限於概念、甚至是翻譯的限制,甚至有一些誤導,造成了兩種工作切換之間有清楚界線的誤解。我非常明白,即便讓小孩留在臺灣,自己去了東大貌似輕鬆自在,但心理的親職機制完全無法暫停。
親職其實是無法按下暫停鍵的生命邏輯
怎麼說「親職」是種生命邏輯?不論小孩有沒有在身邊,隨著年齡成長,親職內涵不再是辛苦的抱哄更換尿布,但轉化為更趨複雜細密的養育照顧。終究我帶著六歲女兒一起到東大進行訪問。秋季到冬季,每日經過柳宗悅創建的民藝博物館、東大校園銀杏大道一起步行上學,是很美好愜意。
但在東京,即便白天讓女兒到大學校園旁的國際學校和同齡小孩玩耍毋須擔心太多(在日本學制起訖計算不同,她的年紀仍視為保育園大班),晚間我們會在晚餐後展開作業,依照臺灣國小班級導師的指示,完成作業。而後我會拍照Line給老師確認。
原以為沒什麼,如此這般我倆大小各自可認真作業個40-60分鐘,還有駒場校區的蟲鳴為背景,應是安寧美好。然而三番兩次,老師回傳指出種種作業明顯錯誤,例如少了聲符、筆順方向顛倒、題目看錯...我才意識到傳作業之前得好好檢查一次(對,我是如此失職沒有概念的家長),甚至,作業時間我其實不得空,至少半副心思要陪伴她理解作業。
剛上小一的小朋友,對於「作業」、「考試」等教育體制基本操作幾乎不能理解的時刻,該花的心思支持少不了。終究,自己還是只能趁著日日早起、摸黑繼續前一晚未竟工作,充分地感受到了駒場月夜星光。
幾個月後結束了東大訪問回到臺灣,女兒也回到臺灣的小學上課,比較熟悉體制的她現在有老師更直接地照顧,一切回到熟悉的狀態是否就可更放心工作了嗎?隔一週,我人在首爾準備對研究經費補助單位作期末報然而開會前第一件緊張不安的事,不是確認簡報, 而是要把握時刻登入系統為小朋友預約寒假活動。剛離開幼稚園的我們,還沒有習慣成自然這般以半學期為單位的超前部署。
再過幾週,我人在牡丹事件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研討會的南臺灣現場,一面聽台上嘉賓的重要發言,一面緊張地準備登入學校網頁,深怕錯過報名下學期社團活動、課後的關鍵時刻。還同時擔心著:如果沒有搶到她喜歡的社團,要怎麼安撫補救?同時還要煩惱她將經歷人生第一場期末考,還要先從解釋何為「考試」和「成績」開始。
持續地和國際學術夥伴確認今年的�交流行程,兩方都在煩惱,六月那趟旅程,我們要不要考慮帶著小孩同行呢?時間、經費、伴侶支持度、目的地條件等等都要細想,弄得好就大小皆歡喜,弄不好就是一場昂貴的災難(當然我們也理解,比起更多高教學院以外的父母, 有此煩惱,本身已經是優越特權的展現)。
終究,想要兼顧學術和親職,代價是高昂的,在 Smith-Carrier et al. (2016)文中有受訪者分享道:「我忽略了其他優先事項(例如我的朋友和健康),以確保工作和孩子優先。」他們訪問的研究參與者普遍表示自己的身心健康受到影響。許多人選擇在清晨孩子醒來前或深夜及週末工作,以彌補育兒責任帶來的時間壓力。然而,這樣的安排對學術工作者的整體健康與福祉造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追趕」狀態,彷彿永遠無法真正迎頭趕上。[3]
儘管我們竭盡所能在職業與育兒生活之間尋求平衡,但我們持續警覺到,即便努力抽出時間陪伴孩子或透過努力安排嘗試兼顧,如同Smith-Carrier et al.(2016)受訪者所說:「我仍然感受到,與他們的關係因疲憊與壓力而受到影響。此外,在陪伴孩子的時候,我總會產生一種應該工作的內疚感」,而在工作的時候,又時時覺得該多些時間陪伴孩子。持續追趕下努力不要狼嗆跌倒,「與子偕行」是多麼珍貴又困難的想望。

同媽媽客座短居東大天天穿過校園很愜意
但是晚上還要寫作業跟上台灣小學進度有點辛苦她了
備註:
[1] 當然不是沒有遺憾,例如在異地想要維持擠母乳習慣,中途就因為繁忙緊張而中止了,當時在岩手縣小旅館中沮喪,但擦擦眼淚還是要走出去和學生們討論災後復興。還好自己早早調適準備放棄母乳執念。回想起來,我比較幸運的是,小孩出生於我已經準備好升等資料的那一年,當時婆婆也還健在,能在台北就近支援;我也不需要擔心因為生養而耽誤升等。但學術追趕和親職戰鬥,當然不只是這一關,如不是我自己的父母和妹妹能在必要時候伸出援手,拼拼湊湊地闖關,路程會更難想像。
[2] 其他相關評論可參考 Guy, B., & Arthur, B. (2021).
[3] 或許是因為這樣,去年我驚訝地被提醒,個人血壓來到人生新境界,至今還沒法找到具體改善的好方法。看似學術工作和親職都嘗試兼顧,但總有哪一塊被犧牲了。
參考文獻
Guy, B., & Arthur, B. (2021). Academic motherhood during COVID-19: Navigating our dual roles as educators and mothers.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27, 887–899. doi: 10.1111/gwao.12493
Lawless, B. (2021). Examining inequitable workload in a time of crisis: A COVID-19 “Sabbatical”.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4(2), 369-372.
Smith-Carrier, T. A., Benbow, S., Lawlor, A., & O‘Reilly, A. (2021). “My only solution is to work later and sleep less”: exploring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ing in academia in Ontario, Canada.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0(8), 930-946.
Urry, J. (2007) Mobilitie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