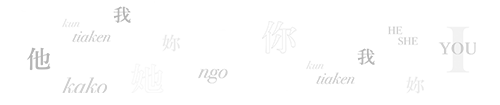Home > 當期視界 > 人類學視界第三十二期 2023.8
知識的雲遊者—黃應貴教授追思會側記
春寒未盡的午後,民族所一樓大廳陸續湧入前來參加黃應貴教授追思會的師長、朋友與同學。現場主視覺是從舊大樓二樓向下垂掛的一幅掛軸,仿若水墨畫的圖面是以黃先生拍攝的東埔社所在之玉山山景為底圖設計而成的,掛軸下方放置了一座以百合、石斛蘭、小莎草、雪柳及枯枝組構成的花藝裝置,襯托主視覺的意象。在掛軸對向的另一側 空間,則以兩張長桌展示了黃先生畢生撰著、主編與翻譯的作品。
追思會致詞來賓區分為機構代表、同事朋友與師生關係三個面向來進行,中間則穿插不同時期的黃先生影像,由鄭 依憶與民族所博物館分別負責腳本撰寫和編輯剪接工作,配樂則由林開世老師建議。
追思學者
民族所張珣所長首先感謝籌備追思會的研究同仁與博物館,憶起黃先生從她在碩士班至完成博士學位後,時時提醒她要留心知識發展的體系並為研究定位,提攜後輩不遺餘力,而黃先生幾乎全年無休地在研究室讀書至半夜的研究精神,因而損及健康,令人景仰。在學術上,黃先生獲得博士學位回台後,開始推動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研究,從人觀、空間、時間與物等,帶領台灣社會與人文學界的 研究者,透過閱讀、田野、研討會與論文審查、修改與出版等過程,成就了本所研究的黃金時期。就制度面來說,黃先生擔任民族所所長時,將以行政功能為主的「組」改 為學術導向的「研究群」,並於2003年全力促成《臺灣人類學刊》的創刊,擺脫了《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的機關研究報告特性,以華文人類學世界的代表期刊自詡,希望最終貢獻華文人類學研究於一個更開放、更廣闊的國際人類 學社群。此外,黃先生提議開辦「人類學營」,第一屆由林 開世負責籌備,希望整合相關研究機構、教學單位與研究 者,透過重要議題的討論,讓人類學的關懷與理念得以向下紮根。
郭佩宜理事長則代表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致詞,指出學會正在規劃進行「台灣人類學口述歷史」系列計畫, 原本希望邀請黃先生,無奈世事難料空留遺憾。首先,黃先生在台灣人類學發展中具有強烈的存在感,因為田野工作、當地人觀點、全貌觀、民族誌、跨文化比較等方面,勤懇紮實地實踐,是後輩難以企及的榜樣。他對布農族的研究是原住民研究的經典,hanitu必定會出現於人觀的討論中,而他談及田野時展現的「愛」會感染聆聽的研究者。《「文明」之路》代表了他對人類學全貌觀民族誌的實踐與具體成果,而他在理論發展的與時俱進,從推動基本文化分類概念所出版的四本論文集,代表了台灣人文社會學界轉向主觀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而退休後更展現了強大續航力,成立「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研究群,為人類學知識 的未來方向設定十個關鍵主題,透過講論會、研討會與論文審查及修改,累積成果。即使與黃先生在某些公眾事務上意見相左,她最珍視的記憶是黃先生聽聞有意思的案例或論述時,眼中閃著光芒且想進一步對話的時刻,那是永遠懷抱初心的、真正的學術人模樣。緬懷黃先生對台灣 人類學所樹立的知識典範和格局之餘,她預告今年九月底在民族所舉辦的台灣人類學會年會將規劃紀念論壇,透過「再閱讀」黃先生的著作來持續與他對話。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林瑋嬪教授則述及黃先生早年在人類系的授課是以社會人類學的四個分支為主,而後在《台大文史哲學報》主編專號開啟了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對話,到了2013 年他轉而關注在新自由主義的不同面向,開設了「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小說與人類學」、「新自由主義與地方社會」等課程,顯現出學思的重大轉折。他的著作仍在系上被教授,對於人類學知識扎根影響深遠;黃先生在台大指導的學生當中,有三分之二回到學界服務。台大更在國際會議廳為他的榮退大作《「文明」之路》舉行盛大的新書發表會,並集結書評出版於考古人類學刊,之後更持續出版「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各單元論文集的書評。最後,身為黃先生1988 年回國後的第一批學生,她提及所受的嚴苛訓練,更意識到黃先生在田野工作、民族誌與理論思辨上的啟發,是人類學界的重要寶藏。
清大人文社會學院榮譽退休教授李丁讚認為黃先生乃是真正學者的典範,數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節奏與嚴謹治學,就為了呈現他對人類社會整體圖像的關懷。黃先生早期曾受到費孝通與社會學影響而以經世致用為念,但不同時期的生命經驗也成為他叩問學術並轉化問題意識的一部分。 進入清華之後,黃先生除了開設了一系列探究新自由主義不同面向的課程,例如日劇、小說、世界民族誌等,同時推動「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研究群,以每年出版一本論文集的速度來推進對於關鍵主題的認識;為了見證第十個單元 的成形,他在大病初癒後勉強參加研討會,卻於首日會議結束後因心臟不適而送急診。在黃先生因為心律不整開刀後而經歷了一段超自然經驗,讓他並不滿意於當前的本體 論轉向討論僅關注人與非人間的關係,希望有時間能夠處 理超自然經驗對於新知識形塑的意義,無奈事與願違。
遠道而來的東埔社伍錐牧師則想起黃教授在東埔做田野時,一大清早就會看到教授站在山崖的身影,就是追思會海報上呈現出的東埔社面貌,當時感覺黃教授應該很重視身體健康。黃教授會與布農獵人一起上山打獵,農忙時他也跟著下田工作,充分體會布農人的生活,對於他的離去 感到非常不捨。黃教授在 1982 年出版的《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一書,送給每一家一本,今早還特地翻了一下,書的封面就是牧師當時牧會的東光教會嬰兒節,不過居民公認黃夫人對布農語的拼音最正確,而黃教授讓人最佩 服之處是他做田野時非常投入與當地人的生活。在牧師心 中,黃教授是人格者,不重視個人名利,希望他永遠安息。
追懷摯友
除了在告別式上對黃先生的追思(請參閱前一篇文章)之外,國立台灣大學博物館林開世館長只補充兩點。第一點是關於黃先生的選擇與分寸。黃先生年輕時是個典型憤青,當年在久美協助當地人成立互助合作社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讓他對社會實踐有所保留,並做了一個重要選擇,即,將生命奉獻於理解社會現象背後的知識性質。因此當時尚未分家的社會所同仁在連署抗議時,就自動跳過黃先生。但黃先生唯一連署過的就是獨台會進入校園抓人事件,因為那涉及學術自由的問題。第二點就是全心奉獻給學術的黃先生並非容易相處之人,甚至將客套發言當成學術論辯,致使現場面面相覷。他認為這種生活方式之所以可能,背後有一個人撐著,一個願意支持、接受甚至欣賞他的人—鄭美能師母,這是我們在紀念黃先生時不能或忘的。
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張隆志館長心中,黃先生是一座堅韌、崇高且深不可測的大山。從碩班到進入台史所之後, 他就是黃先生長期的讀者,之後借調清華後更與黃先生合作進行了課程改革,並共同授課。在與這座大山互動的過程中,對身為台灣史學者的張館長而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黃先生的內本鹿研究開啟了歷史與人類學的對話,《「文 明」之路》更是開啟了臺灣研究與知識的里程碑。而他最感好奇的是關於黃先生後期關於生死的經驗如何挑戰當前知識,相信黃先生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做田野,並以看不見的方式影響著我們,透過不同方式與我們對話。對他而 言,這座大山不會遠離,只會更加深邃。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兼任副研究員陳文德老師則以「亦師亦友,如兄如長」來表達他對黃先生的感謝與緬懷。他回顧與黃先生近四十年的互動與相識歲月中,相較其他人,對黃先生在知識上的態度、對學術同儕和學術環境的期許,有更多層面的接觸與了解。與黃先生在學術的互動,常讓人感到壓力和緊張,因為他提問犀利,用詞直接。黃先生是淡泊名利的學者,執著於知識上的追求與探索,但從不成群結黨。所謂「黃派」這個標籤,對黃先生一生追求學術的真誠與努力而言並非事實,更模糊了他認為學術探討與互動應有的氛圍與心態。陳老師認為自己之所以能以人類學研究來實現個人理念的志業,全是因為黃先生的引領:從1979年服役時接到黃先生來信鼓勵他擔任謝繼昌先生的助理、進入碩班、與黃宣衛老師一同跟著黃先生閱讀人類學的原文經典,而後進入民族所工作,甚至讓他借調至台東大學籌備南島文化研究所,並慷慨給予支援。此外,黃先生在不同研究階段有不同的知識關懷與研究課題,其成果為的是回應當代課題,這也影響了他對卑南族的研究。黃先生對布農族的長期研究展現出人類學整體性思維的 宏觀視野,其著作將是台灣人類學重要的學術資產。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丁仁傑老師認為黃先生總讓人又愛又恨,又非常懷念,他以平行線的角度來說明。互動形式總讓人感覺直接、高傲,像是明星花露水與香奈兒香水不均勻地攪拌在一起,用後殖民的語彙來描述就是:既本土又西方,既反霸權又霸權。他與黃先生有交會、摩擦、擦槍走火的時刻,也因黃先生對新興宗教感興趣而「擦身而過」;儘管立場不同,但他十分佩服黃先生以宏觀架構來定位相關現象。當黃先生因為私人事務有求於他時無比謙和,非得親自處理、致意。有次受邀去清華上課,黃先生展現從未有過的客氣,並說他是荒野一匹狼,非常羨慕他。這些話讓丁老師受寵若驚。他揣測黃先生或許因叫不動他而無奈,或許將追求自由的念想投射在他身上。之後黃先生邀請他評論一篇研究慈濟的文章,促使他寫出新的論文;這讓他開始渴望去上黃先生的課,以獲得新的刺激與動力。如今黃先生仿佛前往另一個平行宇宙,再無法與之交會,但他總感覺這個對知識無比執著,既霸氣又客氣的人,一直在身邊,既不遠離,也不致太近;當他需要研究案例時,就會來找我們。他很希望能再有一個如此特殊又執 著的人,來敲他的門,號召他做事,更希望黃先生偶爾進到夢裡,給予學術上的鞭策、啟發與激勵。
追憶老師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王梅霞教授同樣是1988年修習「宗教人類學」的學生,畢業後擔任老師的助理。除了人類學知識讓人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黃先生對知識、田野與生命的真誠,吸引她進入人類學界。他喜歡談田野故事,特別是他在花壇遇見的田野哲學家,如何以道家精神(這是老師嚮往的境界)默默影響他人,促成農業機械化;又如,跟布農人前往森林救火一事,讓他體悟世界要有傻子才能運作。於她,老師是個不求名利的傻子,一生奉獻給學術和台灣社會。他常從田野現象(如森林中的風聲、夢境)反思自身知識的限制,期許自己能寫出猶如《百年孤寂》的作品,跳脫西方知識的限制,以貼近當地人的樣態。當他開始推動「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研究時,她曾問:為何不以三至四年的時間,針對幾個議題深究以做出貢獻?他回答說: 「我沒有時間了。」頓時她感到時間無情,更感佩他以強大意志完成十年計畫。去年新書發表會後,黃先生儘管體力欠佳,眼中閃著光芒分享出版計劃:日劇、小說與世界民族誌。黃先生留下重要資產是他持續探索未知的熱情;而今他與我們有如身處多重宇宙,以不同方式影響我們。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楊淑媛回憶,最後一次見到黃先生是去年八月《解鎖新「識」界》新書發表會之前,當時 他看來氣色不錯。除了研究,他花許多時間表達對她個人的關心,再三提醒她注意健康,因此當噩耗傳來時,她無法置信。其次,她進入人類學界的契機與黃先生有關。大學時因為劇場而閱讀了Grotowski的貧窮劇場理論,進而對文化產生興趣而報考人類學研究所。在面臨抉擇學校之 際她先去拜訪黃先生,他只是向她客觀分析兩校研究所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她閱讀兩校老師著作,發現黃先生是嚴肅、認真的學者。她從事布農族研究也是因黃先生認為她個性反叛,比較適合平權社會,而當時黃先生起心動念想從事漢人研究。這讓她從年輕學者開始就必須面對黃先生這座大山,而為了要在學界有一席之地,必須不同意黃先生的論點,而兩人的確為此衝突。即使有怨懟、衝突,對她而言,「老師」一詞指的就是黃應貴,再無他人—即使修過其他老師的課。最後,她提及黃先生將歷年來剩下的差旅費當成公積金,提供給像她這樣家境不理想卻想出國深造的學生,讓她感念在心。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許維德副教授回憶去年同時失去愛妻與最敬佩的黃先生,感受到失去另一半的艱辛與痛楚,向師母致上祝福。1989年他就讀社會系二年級開始修黃先生的課,之後旁聽碩班的經濟人類學。日後社會系同學回想起來,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黃先生的課。儘管研究領域差異很大,他申請博士後時去找黃先生而老師二話不說就答應,讓他以自己的專長參與老師當時的整合型計畫。 當他尋得教職離開之前,奉從商的父親之命帶著鮑魚罐頭禮盒送給博後指導教授,以通達人情世故。黃生生得知內情後收下,數日後再以所長離職有送禮需求的名義,回贈兩萬元紅包—因為他只知鮑魚昂貴卻不明白市場行情。黃先生至清大任職後曾與他及家人聚餐,席間試圖與他剛出生不久的女兒互動,顯現出他這十年來的轉性。在他升等後,老師邀請他參加「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系列研究檢討族群與階級的問題,但因對黃先生的孺慕,最後卻變成回顧黃先生對族群概念的轉變,並以涂爾幹的概念來挑戰黃先生對族群是否為社會事實的質疑。在他心中,「老師」只有黃先生一個,至今他的教學方式仍受黃先生影響。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教授葉淑綾對於當年黃先生與陳文德老師籌備成立南島所仍深懷感謝。她念碩一時就與同學一起修黃先生的親屬人類學,承受嚴格訓練,讓學生習得以嚴謹態度面對學術,但求學過程常因黃先生學識過於淵博而導致自我懷疑是否適合學術工作。2004 年前往澳洲攻讀博士之前,師母會到所裡來教她練氣功以強健身體,以面對博士班訓練,同時也主動提供經費,希望她能無後顧之憂地攻讀學位。當時黃先生與師母相當關心學生的學術、健康及生活,有如父母一般。從事教職之後,她更感受到黃先生的研究對布農人的影響力。例如,老師撰寫台東縣史時認識的牧師考取南島所繼續研究布農文化;再如,21年前她隨著黃先生、陳瑪玲老師、夏黎明老師去「尋找內本鹿」,雖看似無功而返,但至今內本鹿尋根活動仍持續著。儘管黃先生前往另一個世界,但精神不曾遠離,提醒後輩在學術路上努力不懈。
身為黃先生中後期所收的研究生,台大人類學系黃郁茜老師因自己治學態度而對黃先生深感愧疚,面對他知識與研究態度上的自律和嚴謹常不禁肅然起敬。首先,黃先生在學術上懷有包含一切所有(all-encompassing)的體系,這是深受他的老師王崧興先生之影響,提醒他創新理論不只是與前人不同,更要「吃掉」前人的理論,能解釋前人無法解釋之處—但學生全都做不到,只能被黃先生龐大的體系吞噬。此外,黃先生重視學術上的誠實,若前輩有錯要勇於推翻。其次,他在田野中善於解讀聚落的空間意義,常說「房子會說話」;從表面現象去解讀當地人未曾意識到的深層的結構意義,是他的思考特點。從空間來看,他那間擁有強大氣場的研究室就是他的心,書架擺設整齊,而他永遠坐在面窗的書桌前讀書、寫筆記,持續至午夜的燈光是讓人心安的標竿。在學術生命上,黃先生展現絕對獨一無二的純粹和嚴格紀律,這有如廣義相對論中的大質量天體,凡靠近者莫不感到時空與運動軌跡被扭曲、改變—即使你不同意、不理會,卻無法否認它的存在。不過與黃先生家人的互動中,她發現老師的另一面:溫暖可親、幽默開朗、活潑健談且單純。事實上家人對黃先生的描述更接近清華學生的印象:對人包容且不侷限可能性,勇於追求心中目標,懷抱對世界的熱愛,即使充滿艱難仍懷抱信念。對她而言,這位自律簡樸、思想高貴且偉大的老師,展現出透過已知有限性、物質性的存在,去了解一個純粹的、不斷向前探索的自我超越之力量和精神。就如林開世老師口中的韋伯,黃先生是將整個時代的力量扛在自己的肩上。至於要如何掌握這個時代以及個人如何理解時代,黃先生有獨特的人類學方法論—來自他所熱愛的Mauss—也就是從平凡無奇事物中找出最廣泛深遠的意義。當然,這需要敏銳的覺察度、嚴謹的學術訓練以及獨特的視野。最後,黃先生關心的問題有如韋伯所言,在時代肅殺的面容之前,能夠毫不軟弱、毫不逃避地去正視它。對黃先生而言,這是所有人都具備且能做到的,只是多數人選擇另一個方式。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洪廣冀老師是在森林系念博士班時,以挑山頭打怪的心態選修黃先生的經濟人類學,之後是歷史人類學。黃先生強調區域這點影響了他,認知到若要了解區域,必須有整體視野以認識其色彩,需要大量閱讀與田野以掌握區域特色,再以比較視野以凸顯特徵。當時年輕人最喜歡的是台社這類以政治經濟學出發去談論階級、壓迫、結構與國家的作品,但他從老師課堂認識到人如何理解世界及其框架、如何行動與實作,並謹記修課只是進入龐大知識系譜的第一步。另外,他曾帶黃先生去爬「南一段」,心想在登山應能勝過老師,卻發現穿雨鞋的老師走超快。不料林道崩塌並受雨襲擊,無路可去之際被迫臨時紮營。此時他看到黃先生雙眼炯亮,神情鎮定,霎時體認到惡劣天候或未能登頂沒什麼大不了,不過是登山的平常,而被成員圍繞的黃先生有如穩定軍心的恆星。最後因老師與上山砍草的布農人攀談並受之帶領,所有人得以脫困。領他入門人類學的黃先生,是他在學術上希望超越的對象,老師宛若漫遊星球的小王子,丟出看似無理的問題,但互動的人定能感受那出自純粹好奇與真心,為之感動、受到引領,直至其聲音、影像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精神科醫師周仁宇博士與黃先生僅有數面之緣,但大學時就以黃先生為偶像,反覆閱讀《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認定老師的作品才是認真的學術。2014 年某天晚上接到黃先生邀請他參加「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的講論,無比興奮的自己只記得回答「好好好」而忘了邀約內容。當時台灣精神分析學會快速發展而不斷膨脹的業務讓他分身乏術,但在黃先生不斷遊說下就答應了,用心理學的說法就是「習得無助感」。然而父親過世讓他異常混亂,忍痛拒絕了黃先生參加研究群講論的邀請,失去一次與黃先生合作、學習的機會。之後黃先生仍不放棄邀請他,讓他與人類學保有聯繫。好幾次,黃先生問他對於人類學與精神分析之間的關係有何看法?雖然他在美國讀人類學,同時接受精神分析訓練,但那些文獻無法讓他感動,也沒有特別的看法。2021 年黃先生邀請他去課堂評論,演講結束後 黃先生表情嚴肅地說:「剛才評論者所以能那樣評論,是因為評論者有自己學習的軌跡與累積。」而他對這段看似讚許的話的解讀是:每個人不但是受益,同時也受限於自己的學習歷程。那一刻,他才真正去反思自己的訓練過程。特別是,他體會到老師從經驗如何抽象化為想像,並影響到下一次經驗,在這個不斷來回的迴圈中獲得成長,其中真正的關鍵在於經驗。他受此啟發並運用於督導,讓督生能夠尊重、肯定正在經驗著的人(個案),不直接提供決定方案,也不棄之不顧。他感覺到老師的偉大是因為他是認真、誠實的人,這樣的人在面對巨大挑戰時,有足夠的能力和毅力去理解那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無法挽回的創傷,從創傷經驗中獲得了悟,為我們帶來溫暖與理解。黃先生過世後,他開始閱讀老師的作品,意識到老師在很短時間內不斷連結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關聯,而這些對他開始產生意義,雖不知會將他帶向何方,但無疑將成為給予他未來思考的養分。
2012年黃先生到清華教書後,施淳益老師(現為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一直擔任課程助教。當年老師在給大一新生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課程前三週的指定閱讀是《「文明」之路》,他特別在第三週的演講語重心長地說:「這是你們的時代,這些問題留待你們來解決。」這構成他清華生活的基調。因黃先生的課不易找到助教,最後全由出身歷史系的他擔任,但每週閱讀量讓他不得不在課後向老師討教。印象深刻的是老師的研究室,隨著課程逐年開設並修改書單,書架上的書慢慢增長、完備,平行 於「新世紀社會與文化」各主題連年接續完成。黃先生的平易展現在以生活化例子向學生解說概念,例如從宿舍寢室從共有垃圾桶轉變至每個人各自擁有的現象,推論出個人化現象和時代的改變。事實上,黃先生剛到清華時正逢 318 前後,他的課有如定海神針,讓學生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特色。此外,老師對當代現象的求知慾讓人很難想像他已年過七十,例如老師受學生之邀去看新海誠的電影後就寫了很長的心得,甚至在課堂上談起「攻殼特攻隊」。某次向老師報告博士論文進度,他才聽聞老師的瀕死經驗,而老師表示找出連結兩個世界的知識形式將是他晚年的主要工作。黃先生在讀畢《雲遊者》之後,自認有把握可以透過文字,以更超然的視角將涵納超自然經驗的知識形式。
曾擔任「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研究群」助理的施以慈(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回想,當初因碩論寫作瓶頸求助於老師而開始熟識。老師曾說喜歡清華那種只有讀書、教學與寫作的單純生活,常與學生在中午時一起下山用餐、聊天。當老師喜歡以智慧型手機拍攝生活風景,特別對紫色小花投注許多感情,甚至某日發現小花被鋤掉而感慨人類對它的輕忽。有次老師與師母、怡君與依憶去福山植物園時,盛開的小花讓他心有所感:「也許,清華不是它的容身之處,所以一有機會就開得燦爛。但在植物園,它竟然有那麼大的空間讓它發揮,卻反而不突顯,人好像也是這樣。」不過,在校園散步時,老師總是選擇最難走的山路,將學生拋在後方,偶爾回過頭微笑地挖苦年輕人體力欠佳,繼續隻身前進—但不斷前進的他卻說自己感到孤單。 乾旱持續的那一年,校園裡相思樹反而更顯燦爛,他有所感地寫下:當植物面臨危機時,就會集中所有養分去開花結果,貯存於種子;如此,到了下個季節就可以延續生命。最近她才體悟到那些話說的是老師自己。老師離去後,同學們以各種方式(參加告別式、法會、拜訪家裡、巡禮老師 的研究室與宿舍和做夢)尋找他;就像老師提醒學生要誠實面對自己,同學們意識到無法再躲在老師背後,必須面對老師交代的生命功課。
黃先生另一位助理清大人類學碩士陳羿融則以在貝里斯拍攝的短片Still Walking來紀念老師。當時她透過林淑蓉老師介紹去擔任助理,結束在廣州的田野後卻苦於不知如何拼湊材料時,老師就問她:這些非洲人賺錢嗎?她猜想老師的意思是他們不賺錢,但「追尋自我」迫使他們從事高風險活動。這促使她開始思考企業家能動性,透過宗教督促自己過好生活的方式,進行不同面向的自我管理。直到最近有報導人分享在非洲的豪奢生活照片,讓她明白為何當初他們願意在中國經歷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因他們相信只要經歷、穿越這些,之後一切就值得了。她曾邀請老師到貝里斯,老師則說若有人類學研究貝里斯的職缺就會去;但那一天始終沒有到來。她領悟到生命是有限度,畢竟人不像罐頭會印上過期期限,老師的有效期限突然就到了。如果人真的能知道死亡的確切時間,那麼每日所作所為和行為的排序,必有所不同。老師晚年常提醒學生要做自己、 誠實面對自己,或許因為老師意識到生命的限度,才再三提醒大家努力做最想做的事情。就像救火的傻瓜,無論旁觀者如何看待,自己問心無愧即可。她感謝老師願意在同學面前展現他不同的一面,對同學們而言,老師無疑是最重要的存在。
最後鄭美能師母向與會的朋友表達謝意。當黃先生因惡性心律不整而終止呼吸時,那段時間她曾經情緒低落。在她心中,他是好父親、是她無話不談的好伴侶。